大学毕业35年了。每每提起,总有一种青春影像在相伴萦绕。扬州师院历史系,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时学校没有大楼,却有大师,总能给我们意外的惊喜;那时彼此尊重,平等对话,师生之间往往能结成忘年交;那时有歌唱、有鼓吹、有表演、有书艺,温暖着每个学子的心灵。那时很单纯,怀抱理想,不乏崇高,那是我一生挥之不去的精神原乡。

扬州师范学院大门
没有大楼,却有大师,总能给我们意外的惊喜
扬师历史系,在1980年代,既没有大楼,也没有像样的房子,只有几间防震棚作为我们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防震棚前是一泓宁静的池塘。当时条件很艰苦,冬天西北风刮起来,用毛竹做成的梁在风中呼呼地响,但我们的教室里,却比较地暖,因为有任半塘这样的大师、葛兆光这样的新锐和我们在一起。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既读书,也读人。
在我们的池塘边,住着一位倔犟的老人。每天清晨,总是准时独悠悠地拄着拐杖散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任半塘先生。记得有一天,任先生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历史系的学生上课。先生蓄着白白的小八字胡子,戴着瓶底盖式的高度近视眼镜,一手举着写着“词”的牌子,另一只手拿起写着“辞”的牌子,从唐戏弄说到唐声诗,从宋词讲到金元散曲。任先生沉浸在他的《散曲概论》、《曲谐》、《唐戏弄》、《唐声诗》和《唐大曲》中。他心中的曲调开在中国礼乐的枝头上,开出了唐代以后士大夫与庶民共同欣赏的词与曲,唱出了一个江山风景、英雄胸襟和万民情怀来。那天,先生讲述了词与辞的区别,并且拿出证据,说周有戏礼、汉有戏象、唐有戏弄,颠覆了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的“宋以前没有戏曲”的观点。记得先生那天自信地说,敦煌学不在日本,而在中国。任先生的《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歌辞总编》,就是他理想的最好行动注脚。先生独立思考,淡定读书,从容研究,坐拥书城,南面而王,成为国学之山。他以中国特有的世情之美和新鲜知性,引来了一场散曲的新的活气,为研究中国戏曲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怎么也不会忘记,1984年,我第一次见到葛兆光老师时的那个场景。那时的他刚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当时我是班长,因为他带来的书比较多,所以我带了几十个同学,把他50多箱书一一扛到了他的宿舍。他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特地给我送了一本走向未来丛书。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本卡普拉写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扬州师院东门边的池塘

任半塘先生雕像
那时,正好赶上中国的文化大潮和中国的思想启蒙,巨大的热情和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是1980年代的风尚,时代重回五四,而葛兆光先生恰好是那个时代的先锋式人物。他给我们讲授的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从中国儒教到中国道教,从中国道教到中国佛教,教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尤其是在1985年,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吹皱一池春水,引发了中国读书界一场方法论大讨论。葛先生擅长精雕细刻,有强大的意志力,是一个在很少有人问津的一摞又一摞的故纸堆中磨练出自己的意志、把研究当成了最大乐趣的人。深受先生的精神影响,当时我们白天不知黑的夜,如饥似渴地读书,从中国读到世界,读经典、读原著、读第一手资料,做笔记、拟大纲、写心得体会,感觉到世界就在我的胸怀里,我用我的眼睛去看世界。那个时代,没有读过李泽厚写的三卷本《中国思想史论》,没有读过走“向未来丛书”,就不算真正的大学生;没有读过钟叔河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就不算真正的文科生。我们从《人的发现》,在《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读到《激动人心的时代》,不断《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追求《人的现代化》和《新的综合》,探寻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我们今天回顾那个时代的时候,至今还会为当时的精神追求感到热乎乎的。
当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是重读,重读诗经,重读儒家,重读中国近代,而且是在消化了不少西方人看传统中国的基础上的一次重读。当时我们追求真理的热度到底热成什么样?我想,用汤因比《历史研究》里面的话,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当时我们的心路历程:“人要每日每夜去争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地狱与天堂两股势力之间的遭遇仅仅是序幕,大地上某个人的激情才是这出戏的实际内容。”“我决心离开这块岩石,攀登眼前这道峭壁,抵达上面那块凸石。我打算这样做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充满风险,但我已把安全置之度外。我明白一旦我止步不前,我就会坠落下来。一旦我坠落下来,我就会粉身碎骨。但是为了可能的成功,我宁愿冒这种不可避免的风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远远超出了我们能够显示的东西。”“世上的健儿,把它重建得更加壮丽,建设在你们的胸怀!再以明朗的心神,重新把人生的历程安排。”
激情冷却下来终归是理性。望着五四新文化回潮的背影,在没有大楼,却有大师的日子里,我独守着一泓宁静的池塘。在人人都在走出中世纪的大潮下,我独以为要走回中世纪。1905年废科举,绅士没了;1919年五四运动,儒家没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文化没了。我们总以为越彻底越过瘾,而结果恰恰是失去的要比得到的要多很多。中国传统有好的地方。比如,从个人来讲,是尊重人的生命和实践爱;从社会来看,是重视人与人的信义与和睦。中国以家庭共同体意识为基础,实践对人类的爱和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我们需要孔子,需要一个有如孔子大造生意一般的丰富生活。其实,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中国代表着世界时尚。伏尔泰向启蒙时代的欧洲展示的《赵氏孤儿》,代表着一种中国精神。那么,这个精神是什么?我感觉到是忠义、尽责和敢担当!正是这种精神,照亮了当时整个西方世界。今天我们应当回归中国精神,重新拿出这张名片递给世界。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对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因此,当年我以扬州学派的殿军刘师培思想作为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每天泡在图书馆里,研读刘申叔先生遗书,努力从扬州学派的个案分析中,寻找出一种来自民族骨子里的自信来。
彼此尊重,平等对话,师生结成忘年交
扬师历史系,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一个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师生组成的知识共同体。虽然那时还不知道春秋战国稷下学宫是什么模样,也没有真正体验过宋代西园雅集的感觉,但是当时师生互动是经常有的事,成为一道精神的风景。
扬师历史系那时的鼎盛,与祁龙威先生的执掌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原因,一是先生有胸怀,能纳才。像葛兆光这样的年轻老师是他慧眼识才引进的。当时,顾敦信老师治中国考古学、常振江老师治魏晋南北朝史、张锦贵老师治中国近代史、李永采老师治史前社会史、杭舟老师治世界近代史,沈学善老师治战后国际关系史、赵苇航老师治中国历史地理、贡久谅老师治中国历史文选。这一群身怀独门绝活的老师,都是祁先生通过各种办法延揽进来的。他们个性鲜明,彼此之间开展富有生命的精神交往,给学生充实而丰腴的知识膏粱。二是先生有名望,有感召力。祁先生不单有扬州学派的自家风光,在他的周围,以开门弟子华强先生领衔,集聚着田汉云、赵昌智、陈文和、张连生和谢思诚等读书种子。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的胡厚宣、卞孝萱、戴逸、刘杰等一批学界大家,祁先生也是随请随到,经常跟我们讲课交流。祁先生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每次这些客人来扬师历史系,先生总是要请他们到他家里去吃吃饭、喝喝酒、品品茶,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他最后离世。三是先生有人缘,很厚道。祁先生对朋友和学生的好,在系里系外是出了名的。只要你有什么问题,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他都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满心满意地帮你解决。祁先生是治太平天国史的大家,有着乾嘉学派之功。先生每次跟我们上课,总是面对面地交流,有问必答,有书院味道。他总是拿着一本记录着他的讲课要点的练习本,捧着一杯只有几片茶叶淡淡的茶,操着一口常熟话授课。师生之间人格平等,虽有专业知识之间的悬殊,却能保持良好互动。记得当时我作为系学生会主席,主编我们系学生会办的《春秋》杂志。这是师生之间富有生命精神交往的一个平台。王永平老师谈竹林七贤,冯春龙同学论文艺复兴,徐俊祥同学说诸子百家,惠风和畅,温馨感人。祁先生的宽容性格和沉稳才情,深刻影响了其执掌的历史系。当时先生与学生都铆足了一股子劲,欲与天公试比高,有着很高的学术抱负,把刻苦当成了人间乐事。
一个人在人生的出发点上,可遇到的贵人不是很多,而我有幸遇上了。在扬师历史系,我遇到了提携我的贵人许卫平老师。我们萍水相逢,之前彼此并不相识。而我一进校,许老师就让我做班级的临时召集人,后来当班长、做系学生会主席,再后来,又第一个入党,被推荐到扬州师院做学生会副主席。我在扬州的成长与发展,与班主任许卫平老师对我的提携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其实当时我感觉我考上扬师历史系,并不是我的理想学校,主要原因是自己高考没有发挥好。在我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是许老师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正是许老师对我的充分授权和信任,当时我和班委一起,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可以让许老师两个月不到班上,而班级里照样太太平平。记得当时班上夏晓臻和黄立同学家里突然发生特殊困难,我就组织全体同学自发捐款,并把捐款亲自送到这两位同学的老家。班主任许老师对我的终身大事也很关心。当时我对一位女同学有点好感,许老师便私下里和我做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在学术上,许老师治文献学与方志学,旨在重现扬州学派风格。我们常常为了一个学术问题,讨论到深夜。我们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忘年交,直到他去世。此前,我特地从上海驱车到南京肿瘤医院去看望他,分别的时候,他一直把我送到医院的电梯口。此情此景,终身难忘。人,其实最难做到的,是精神的长大。从许老师那里我学到最多的大概是这一点。
在扬师历史系,周新国老师是我的恩师。他当时教我们中国近代史,不仅课上得好,而且功夫也做得扎实。他讲起课来总是那么慢条斯里,但总是那么有道理。无形之中,渐渐培养起我对中国近代史的浓厚兴趣。后来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继续攻读中国近代史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与周老师当年的启蒙有着很大的关系。那时为了中国近代史,我到周老师家,请教周老师的问题,可能是同班同学中最多的了。我们心心相通,每次见面总是那么默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本真的力量让我感染。我和周老师常来常往,每次神会都成了一场场心有灵犀的文化现场,无论是他指导我和彭雪梅同学一起撰写扬州师院成克坚校长的回忆录,还是他在我工作后曾经亲自到盐城师专专程看望我,并想调我回扬州,我从周老师身上真实感悟到了人应该心得本原,保持本真,才能开掘多重自我,人生才有意义。相处久了,周老师的性格也影响了我——总是那么一脸欢喜,又宁静无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为的是什么?归根结蒂,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周老师的人生感悟,从深处讲,是经历岁月磨难后的纯净升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的创世纪。只有以追求纯净为目的,只有在心灵安静之时才能真正做到懂得和接受。
歌唱鼓吹,表演书艺,总有一种温馨滋润心灵
文革之后读大学,那时艺术的生活样式重回社会的怀抱,世道重新有了对物的亲切、对人的亲切。天地清明,时代敞亮。那时的扬师历史系,不只有硬邦邦的知识,而且有生气活泼的各种艺术熏陶,每天生活充满着乐趣,构成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共同体。
“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这颗小树。”当时我们是唱着台湾校园流行歌曲走进大学的。那时的我,每天早晨起来跑步,在淡淡的晨雾中,听得一些老扬州,一边沿着古运河河边锻炼,一边吊着嗓子,练着维扬清曲。
当时扬师有着各种各样的艺术熏陶。如今留在我记忆深处的,首先是黄河老师为我们特别开设的《中国民歌史》。从黄老师那里,我第一次知道《码头工人之歌》的创作故事,是聂耳同朋友在黄埔江边散步时,受码头工人劳动号子的触动而谱写出来的。这是上海最早的工人之歌,也是上海开埠以来最经典的歌曲之一,现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第一次欣赏一代宗师萧友梅先生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问》:“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年华如水?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这首没有华丽语言的歌,直叩深刻的人生内涵。我第一次知道代表中国民歌标志的歌曲《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原来来自于扬州民间:“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香不过它,我本待摘下它,戴又恐看花人骂,茉莉花,茉莉花。”
其次是徐湘老师和王葆森老师对我在音乐艺术教育上的影响。徐湘老师让我在钢琴上校音,王葆森老师教我声乐。当时,徐湘老师还特别请来了扬州市文工团的谈伯林老师教我吹笛子。当年拿着碗,里面放着水,练习单吐、双吐和花舌,别提有多枯燥了。单是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就不知道练了多少遍。
忘不了1985年的那个冬季,天上飘着雪花,我们这些文艺青年齐刷刷地聚到扬州师院人防会堂,津津有味地听著名演员谢芳给我们讲电影艺术。当时导演在扬州瘦西湖畔为电影《文成公主》拍外景,谢芳在里面扮演乳母,我们当中一些同学也被邀去做群众演员。在电影拍摄的空隙之间,我们特别邀请了谢芳来扬师讲电影艺术。我从谢芳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电影是导演的思想在银幕上的一种流动。
更不能忘记的是,在读大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排演历史话剧《强项令》。剧本是蒋明宏老师亲自改编的,话剧也是蒋老师导演的。彭雪梅同学扮演湖阳公主,殷俊同学扮演光武帝刘秀,京都洛阳令董宣由我们下一年级的高学军同学扮演,我扮演戏份比较多的、行凶作恶的家臣。由于在排演时我经常笑场,搞得蒋老师啼笑皆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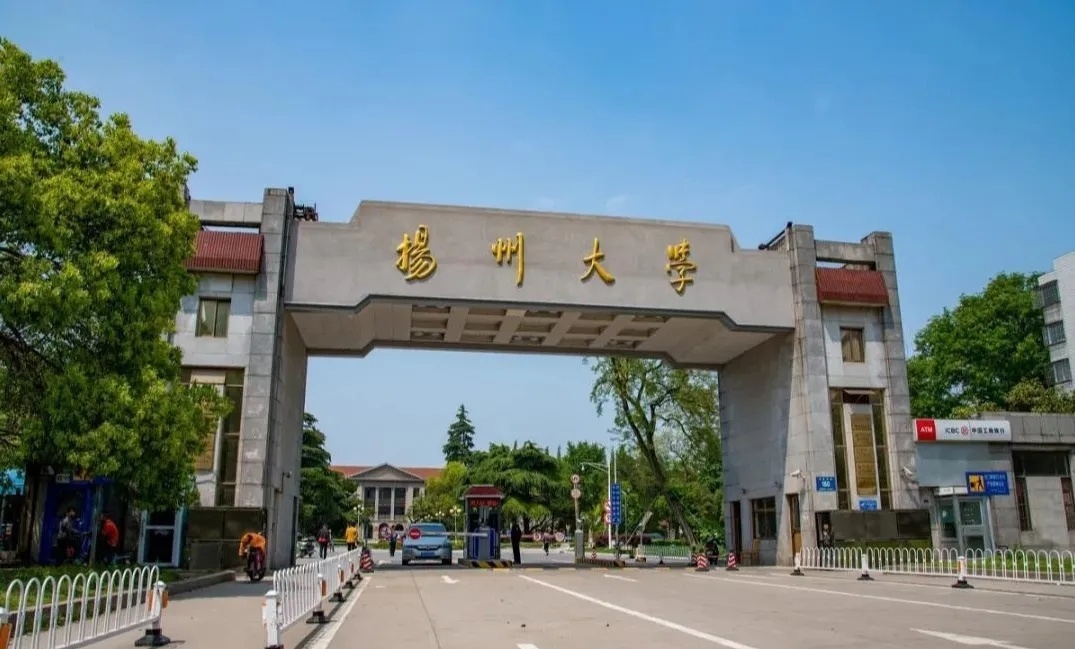
在扬师的日子里,除了经常有艺术的熏陶外,每天还有书法相伴。
我对书法的爱好,起源于小学。那时候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共同负责出学校的黑板报,陈永茂是我小学的美术老师,擅长隶书。到了扬师,又有幸结识了书法家秦子卿老师,他是秦少游的后人,人很儒雅,给我们专门讲授中国书法史。他行草隶篆,笔走龙蛇,气韵灵动。那时我和我们班的书法家黄立同学探讨书法,每天和我们寝舍的同学一起练习书法,大学四年如一日,成为一种习惯,成为我们寝室的一个标签。当时我把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和张迁碑,读了几遍,也练了几遍。四年八个学期,我的书法得奖作品,在扬师学生报上登载了多次。当时由于我担任扬州师范学院学生会副主席,主要负责大学生文科22个社团,所以,经常有机会到扬州国画院,去欣赏李亚如和王板哉的作品,又有机会到南京国画院,亲识书法名家武中奇、尉天池和萧娴,并欣赏他们的作品。
大学时代,我们拥有的物质生活虽然显得贫寒,样子也比较土,但日子过得灿烂。每天的时光不紧也不慢,有时间就去泡图书馆。师生之间,既宽松,又自在,不时有生命的精神交往展开,对话和争论是常有的事。同学之间在宿舍熄灯后的神聊,至今余音绕梁而不绝。如今的我,也只能看着扬师历史系的背影,远远地眺望。失去的,就再也回不来。
扬师历史系,是我知识成长的摇篮,也是我精神成长的原乡。
本文作者杨小川,1982-1986年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历史系,后赴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宣教部部长、生活保障部部长,中国宝武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部长。曾先后任宝钢股份首席文化管理师、宝钢股份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企业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宝钢股份机关党委书记、宝钢集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企业文化部副部长,宝钢集团品牌总监,宝钢集团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法律部部长。因创立中国宝武企业文化标准、B TO B企业品牌标准和企业员工综合目标发展体系而先后荣获黑带大师、文化首席、财大职业导师、优秀党员。此外,担任上海扬州商会顾问、上海曹鹏音乐中心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