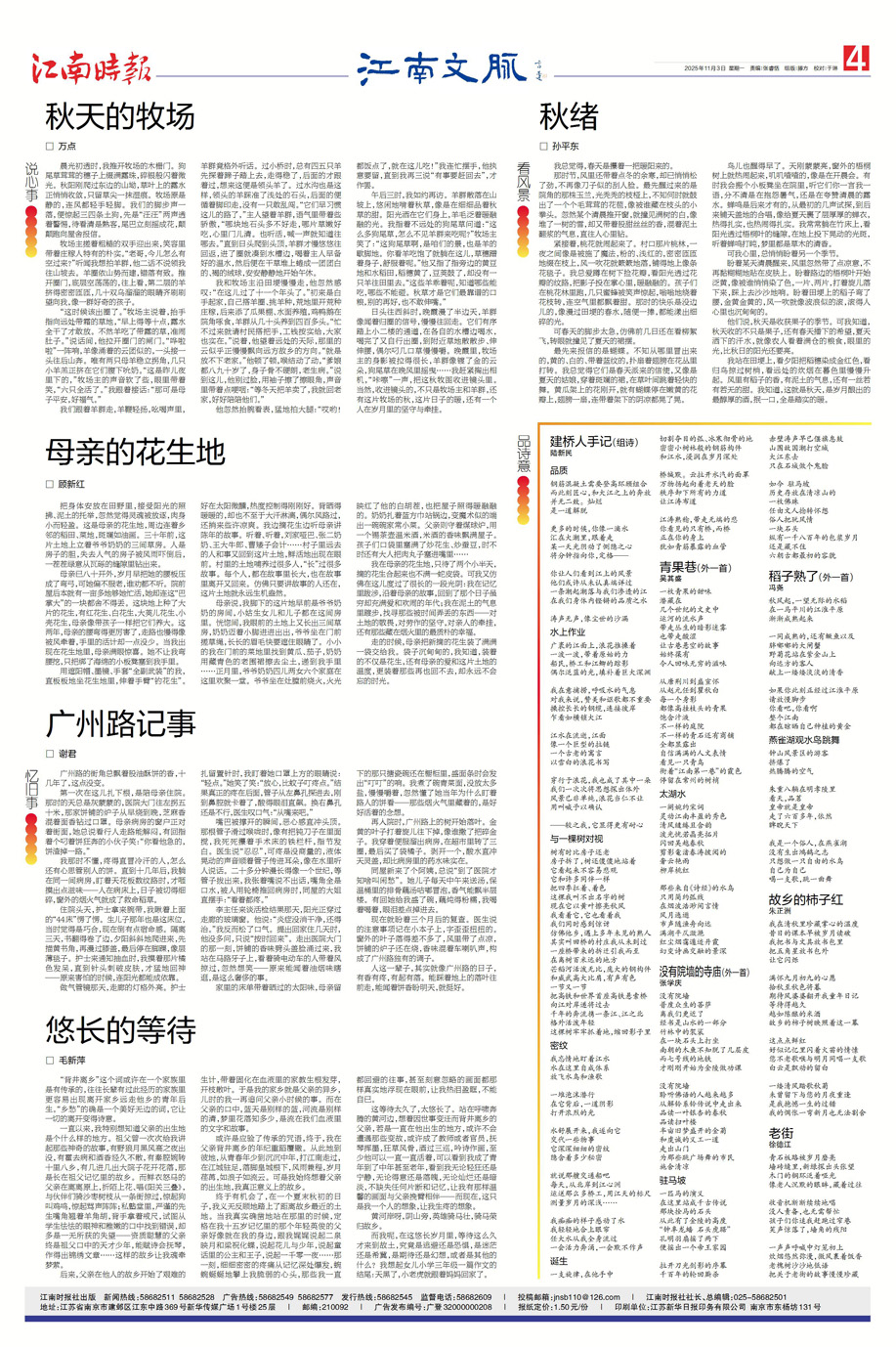秋天的牧场
□ 万点
晨光初透时,我推开牧场的木栅门。狗尾草茸茸的穗子上缀满露珠,碎银般闪着微光。秋阳刚爬过东边的山坳,草叶上的露水正悄悄收敛,只留草尖一抹湿痕。牧场原是静的,连风都轻手轻脚。我们的脚步声一落,便惊起三四条土狗,先是“汪汪”两声透着警惕,待看清是熟客,尾巴立刻摇成花,颠颠跑向屋舍报信。
牧场主搓着粗糙的双手迎出来,笑容里带着庄稼人特有的朴实。“老哥,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听闻我想拍羊群,他二话不说领我往山坡去。羊圈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推开圈门,底层空荡荡的,往上看,第二层的羊挤得密密匝匝,几十双乌溜溜的眼睛齐刷刷望向我,像一群好奇的孩子。
“这时候该出圈了。”牧场主说着,抬手指向远处带霜的草地,“早上得等十点,露水全干了才敢放。不然羊吃了带露的草,准闹肚子。”说话间,他拉开圈门的闸门。“哗啦啦”一阵响,羊像涌着的云团似的,一头接一头往后山奔。唯有两只母羊稳立拐角,几只小羊羔正挤在它们腹下吮奶。“这是昨儿夜里下的,”牧场主的声音软了些,眼里带着笑,“六只全活了。”我跟着接话:“那可是母子平安,好福气。”
我们跟着羊群走,羊鞭轻扬,吆喝声里,羊群竟格外听话。过小桥时,总有四五只羊先探着蹄子踏上去,走得稳了,后面的才跟着过,想来这便是领头羊了。过水沟也是这样,领头的羊踩准了浅处的石头,后面的便循着脚印走,没有一只敢乱闯。“它们早习惯这儿的路了,”主人望着羊群,语气里带着些骄傲,“哪块地石头多不好走,哪片草嫩好吃,心里门儿清。也听活,喊一声就知道往哪去。”直到日头爬到头顶,羊群才慢悠悠往回返,进了圈就凑到水槽边,喝着主人早备好的温水,然后便在干草堆上蜷成一团团白的、褐的绒球,安安静静地开始午休。
我和牧场主沿田埂慢慢走,他忽然感叹:“在这儿过了十一个年头了。”初来是白手起家,自己搭羊圈、挑羊种,荒地里开荒种庄稼,后来添了瓜果棚、水面养殖,鸡鸭鹅在院角啄食,羊群从几十头养到四百多头。“忙不过来就请村民搭把手,工钱按实给,大家也实在。”说着,他望着远处的天际,那里的云似乎正慢慢飘向远方故乡的方向。“就是放不下老家。”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爹娘都八九十岁了,身子骨不硬朗,老生病。”说到这儿,他别过脸,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声音里带着点哽咽:“等冬天把羊卖了,我就回老家,好好陪陪他们。”
他忽然抬腕看表,猛地拍大腿:“哎哟!都饭点了,就在这儿吃!”我连忙摆手,他执意要留,直到我再三说“有事要赶回去”,才作罢。
午后三时,我如约再访。羊群散落在山坡上,悠闲地啃着秋草,像是在细细品着秋草的甜。阳光洒在它们身上,羊毛泛着暖融融的光。我指着不远处的狗尾草问道:“这么多狗尾草,怎么不见羊群来吃呢?”牧场主笑了:“这狗尾草啊,是咱们的景,也是羊的歇脚地。你看羊吃饱了就躺在这儿,草穗蹭着身子,舒服着呢。”他又指了指旁边的黄豆地和水稻田,稻穗黄了,豆荚鼓了,却没有一只羊往田里去。“这些羊乖着呢,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碰。秋草才是它们最靠谱的口粮,别的再好,也不敢伸嘴。”
日头往西斜时,晚霞漫了半边天,羊群像闻着归圈的信号,慢慢往回走。它们有序踏上小二楼的通道,在各自的水槽边喝水,喝完了又自行出圈,到附近草地散散步、伸伸腰,偶尔叼几口草慢慢嚼。晚霞里,牧场主的身影被拉得很长,羊群像镀了金的云朵,狗尾草在晚风里摇曳……我赶紧掏出相机,“咔嚓”一声,把这秋牧图收进镜头里。当然,收进镜头的,不只是牧场主和羊群,还有这片牧场的秋,这片日子的暖,还有一个人在岁月里的坚守与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