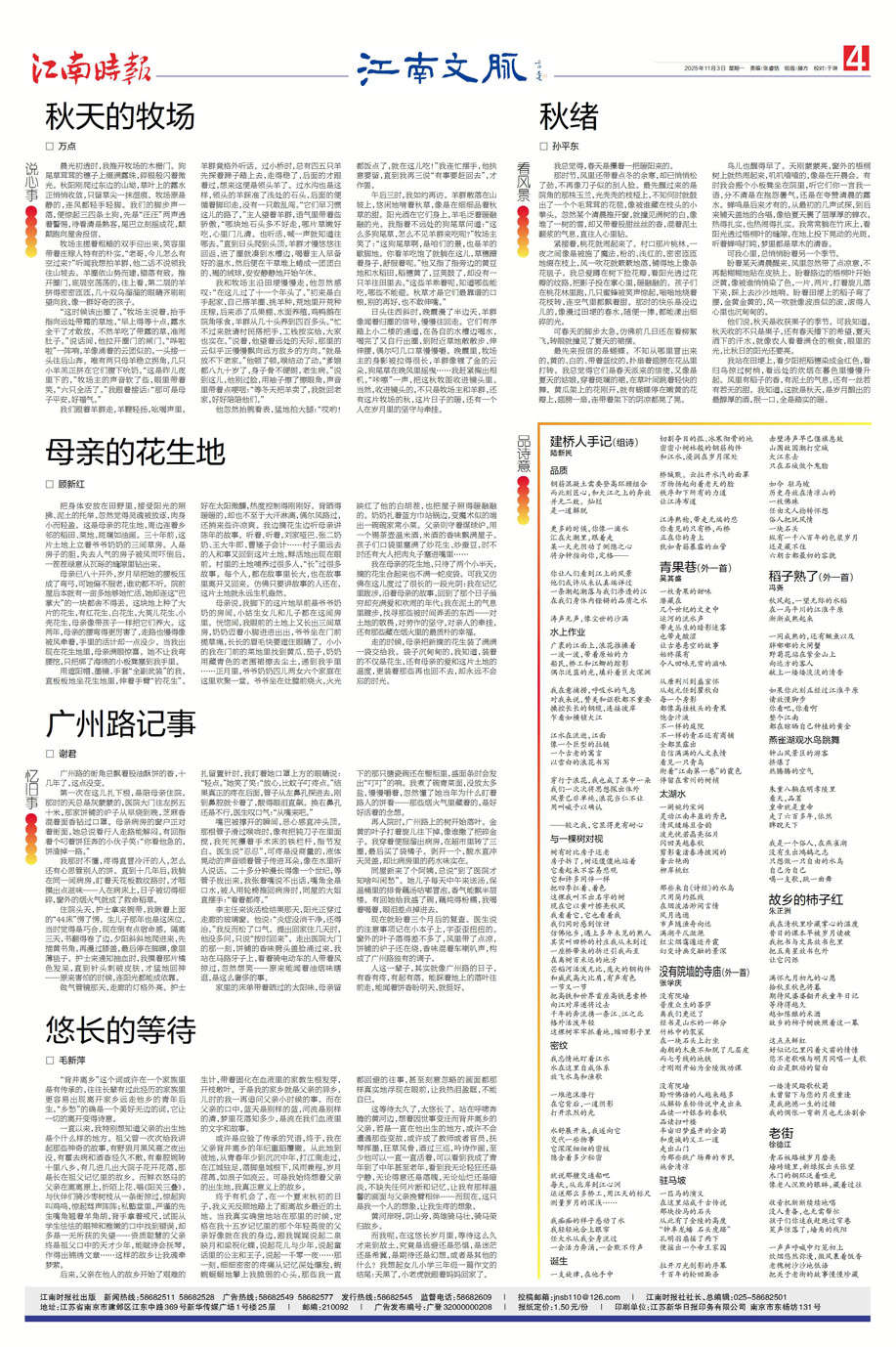母亲的花生地
□ 顾新红
把身体安放在田野里,接受阳光的照拂、泥土的托举,忽然觉得灵魂被放逐,肉身小而轻盈。这是母亲的花生地,周边连着乡邻的稻田、菜地,斑斓如油画。三十年前,这片土地上立着爷爷奶奶的三间草房。人是房子的胆,失去人气的房子被风雨吓倒后,一茬茬绿意从瓦砾的缝隙里钻出来。
母亲已八十开外,岁月早把她的腰板压成了弯弓,可她偏不服老,谁劝都不听。院前屋后本就有一亩多地够她忙活,她却连这“巴掌大”的一块都舍不得丢。这块地上种了大片的花生,有红花生、白花生,大荚儿花生、小壳花生,母亲像带孩子一样把它们养大。这两年,母亲的腰弯得更厉害了,走路也慢得像被风牵着,手里的活计却一点没少。当我出现在花生地里,母亲满眼惊喜。她不让我弯腰挖,只把绑了海绵的小板凳塞到我手里。
用遮阳帽、墨镜、手套“全副武装”的我,直板板地坐花生地里,伸着手臂“钓花生”。好在太阳微醺,热度控制得刚刚好。背晒得暖暖的,却也不至于大汗淋漓,偶尔风路过,还捎来些许凉爽。我边摘花生边听母亲讲陈年的故事。听着、听着,刘家哑巴、张二奶奶、王大牛郎、曹矮子会计……村子里远去的人和事又回到这片土地,鲜活地出现在眼前。村里的土地哺养过很多人,“长”过很多故事。每个人,都在故事里长大,也在故事里离开又回来。仿佛只要讲故事的人还在,这片土地就永远生机盎然。
母亲说,我脚下的这片地早前是爷爷奶奶的房间,小姑生女儿和儿子都在这间房里。恍惚间,我眼前的土地上又长出三间草房,奶奶迈着小脚进进出出,爷爷坐在门前搓草绳,长长的眉毛快要遮住眼睛了。小小的我在门前的菜地里找到黄瓜、茄子,奶奶用藏青色的老围裙擦去尘土,递到我手里……正月里,爷爷奶奶四儿两女六个家庭在这里欢聚一堂。爷爷坐在灶膛前烧火,火光映红了他的白胡茬,也把屋子照得暖融融的。奶奶扎着蓝方巾站锅边,变魔术似的端出一碗碗家常小菜。父亲则守着煤球炉,用一个锡茶壶温米酒,米酒的香味飘满屋子。孩子们口袋里塞满了炒花生、炒蚕豆,时不时还有大人把肉丸子塞进嘴里……
我在母亲的花生地,只待了两个小半天,摘的花生合起来也不满一蛇皮袋。可我又仿佛在这儿度过了很长的一段光阴:我在记忆里跋涉,沿着母亲的故事,回到了那个日子虽穷却充满爱和欢闹的年代;我在泥土的气息里踱步,找寻那些被时间弄丢的东西——对土地的敬畏,对劳作的坚守,对亲人的牵挂,还有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最质朴的幸福。
走的时候,母亲把新摘的花生装了满满一袋交给我。袋子沉甸甸的,我知道,装着的不仅是花生,还有母亲的爱和这片土地的温度,更装着那些再也回不去,却永远不会忘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