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掠过未名湖的翅膀
——读《北大与时间之外》
期待中的卞毓方先生签名本《北大与时间之外》终于到手了。有种读书体验,当手中捧着的是你喜爱的作者签了名字的书时,便更加产生一种与作者的沟通感、亲近感,感觉能让你更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你在这端仰望着,他在那端注视着。
一如以往读先生书的感受,扑面而来的是大气游虹、清风出袖的文气,黄钟大吕、独树一帜的格调。
这可谓是一本“回忆录+”的散文集。全书共分六辑,前面的一、二、三辑是作者“回忆”自己的长成录、思想录,后面的四、五、六辑“+”的则涉数十位北大的精英。每辑都有写在前面的引言,带着你一页一页地走进作者“以北大为杠杆”撬开的那一砣砣“凝固在时间之外的时间”,走进那个“超脱具体岁月,囊括既往,直观现在,透视未来”的北大。同时,也走进了一个“成也北大,败也北大;爱也北大,痛也是北大”的步履途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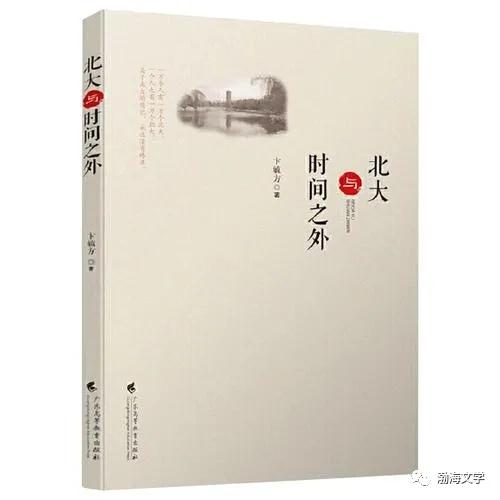
壹
在“头顶一片白花花的光亮”的那砣时间里,看到的是一个“末代私塾生”是如何“七拐八拐就拐向了北大”——仿佛冥冥中有只无形的手。
五岁那年,白胡子的祖父把他送进了同样长着白胡子的私塾先生那里。那年该是1949年,当时新中国已明确了对私立教育的改造方针,三年后,全囯的私立学校或由政府接管改为公立或自行关闭,作为私学之一的私塾从此也关门大吉。
“末代私塾生”及时插班进了公立学堂,一路念到了射阳县城里的中学。读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正值茁壮成长之际,人生中的“变故”摩肩擦踵而至——社会的、家庭的、自身的,最终让他回到小镇的家中,等待他的是辍学。
在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先是凭一位来到家里的道士的一道纸符,治愈了让他卧床一月之久的毒疮,一场大病被莫名其妙地化解了。接着,家里又来了他的班主任老师,说服了因祖父离世而占居上风的“主工派”(让他退学回家干活),使他在第二年秋天又得以重返学校。对那道士之术,他一直搁在心头无法解释;对他的班主任,则是“季老师挽救了我,我一辈子都记着他的大恩。”
也是那场大病之后,让他之前当运动员、当画家的梦想改弦更张。他甩掉了标枪,放弃了画板,扑向了书卷。
他晓得“北大”时是1959年,那年射阳中学有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有两人考上了北大,打那起,他才知道北京有个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
读到高一时,他先被分在学英语的丁班,一周后,学校重新分配,把他调到学俄语的乙班。后来,他那届毕业生考上北大的四个人都是俄语班的。
“以宇宙之大,之古,之玄奥,之无解,我无法排除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着每个人向前走。”
就这样,他在那只无形的手牵引下,七拐八拐地走进了北大,开始了他的末名湖畔的五年时光。书中,他把在每一次拐弯时出手相助的贵人都铭记于心。大爱无言,大音希声。
闭目沉思: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程中,是不是也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引着你,有一些贵人在关键时刻相助着你?
在这坨时间里,七岁的私塾龄童,为邻里代写书信,还凭音推出“皇甫弘毅”的名字,被人称为“小先生”;“一条手缝的红领巾”,让他体味了人性的丑恶美善;一本《镜花缘》,留住了那一代人,那一份自由阅读的空气……
我追溯到,在卞毓方先生文章笔墨中散发出的那份浓重而纯粹的古风古韵,及涉笔成趣的经典文化的意象渊源,那根竟是扎在“末代私塾”的园地里。
我还意外地解开了之前对先生生活中不烟、不酒、不茶的“三不”疑惑。书中道破因由后,他又嘻言诠释:因原本不是北大的料,侥幸闯进了北大的门,上帝为了平衡,就从我应享受的尘世福泽中,剔除了烟酒茶三味。省身醒事,先生如是。

贰
接下来是在“时光深处,尘埃之上”的那段岁月。
来到北大,他登上了未名湖的湖心岛,那一刻,他才感受到“在湖心岛读书,觉得自己已是北大人。” “听一位中年女士朗咏我不懂的外文,彻悟她身后的未名湖水之深”。
未名湖本无名,乃钱穆先生当年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所起。据钱穆《师友杂忆》中载:由于大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便只好用“未名”二字为校园中的那一泓湖水命名。这泓湖水,沉浸着当年燕京大学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又融汇了沙滩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在他跨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刹那,他感觉到校园里所有的空地都站满了人,所有的窗口都挤满了人,所有的建筑顶上也是人挨人,北大历史上的人都聚齐了。仿佛仰脸对了晌午的太阳,令他目眩神迷。那日,是他生命里程中的重大节日,一切都是彩色的画面!
然而,在他满打满算只念了一年零九个月后,一场自上而下的飓风,刮去了他眼中的色彩,一张大字报,使北大成为一场浩劫的漩涡中心——充满彩色的画面,变成了黑白的底片。
“满天浮云,是老天的大字报。”
“文化正在(暗地里质疑)革命。”
“无头脑者的头脑最进步。有思想者的思想最落后。”
未名湖上风雨飘摇。
一次班级常规学习的发言,被急于建功的工宣队师傅断章取义地制造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他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学生”,被视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
大牌美学家朱光潜弯下腰,把脸贴近大便池,一把一把地掏着里面的污垢,搁入几乎与他等高的大竹篓,弓腰背起,只见篓,不见人。
学术大师季羡林,“工人阶级”斗完了,“革命群众”斗,革命群众斗完了“红卫兵”斗,口号、耳光、拳打、脚踢与声俱来。
校园里,批斗、串联、文攻、武卫此起彼落,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浪更比一浪高……
天昏地喑,一时让他说不出“黑夜的黑和白天的白”。
“学业打了水漂,连文凭也没有”,“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虚抛了大把光阴”。入学时葵花乍放的那种金黄亮艳,变成离校时遍地落叶的枯黄憔悴。
将洒落在文中的叙事稍加整理,便可窥出那“大把光阴”都去哪了。
1964年8月进入北大;
1966年5月“文革”开始,8月开始全国大串联;
1967年夏,回老家蛰伏一年;
1968年夏,奉召归校;
1969年秋,搞战备疏散到延庆;
1970年3月“毕业”离校,被送去湖南省西湖农场。
时光深处,唯能让他庆幸与安慰的是:“在那个发疯的年代,我始终没有发疯;在那个迷惘的年代,我终于走出迷惘……感谢上帝把我塑成了我:正因为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崛起,才诞生了我今日的文风和人格。”正所谓:爱也北大,恨也北大。
书中的这坨北大时光,是一个北大人的经历,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历,更是先生这代人的噩梦和创伤。
读至此,不由联想起季羡林老先生的《牛棚杂记》,里面详细记述了他在那段岁月中的各种遭遇,似一面镜子,从中可见恶善丑美,黑白可辩地昭示着后人。读卞毓方先生的这坨“时光深处,尘埃之上”的岁月,也有着同样的镜鉴。
顺便也想起了北大的那个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她已于2019年死了。作恶于人,又被恶所作。书中有对聂的瞬间记叙:她刑满释放后,“我去看她,出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一日,请她吃大餐,她心血来潮,冷不丁冒出一句:‘你一定是公社的’。 ” 她说的“公社”,应该是当年以她这位“老佛爷”为首的红卫兵组织“新北大公社”。2005年由聂口述,他人记录,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聂元梓回忆录》。据说,是一本为自己正名的传记。又据说,这书出版时未经她审阅,她死前手边留存的那本书已经被她翻烂,许多地方夹着书签,书上满目了线条和修改痕迹,那是她认为再版时需要增补的地方。还能再版吗?

叁
自先生离开北大起,仿佛仍然有一只无形的手牵着他,风雨兼程中,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他二十多年后的回归。
他在《未名湖中燃烧的荷花》文中自述:“告别燕园之际,潜意识趁我不备,把我的心悄悄留在了那里。” 于是,他隔三差五地梦见未名湖,梦见未名湖千朵万朵燃烧的荷花,梦里他身轻如燕,一纵身就能凌空飞过湖面……偶尔在荷花丛中荡舟,偶尔梦见在湖心岛东头石舫上垂钓,这印象是在西湖农场烙下的,这场景却被梦挪移到了燕园。
还有,那长沙新车站报时的钟声,也像似响自未名湖南岸的钟亭,水波一样地漫过街道,漫过院落,漫过窗棂,漫过他的心田,余音袅袅不绝。
1970年3月,先火车、后轮船,将他们一行两百多号被集体扫出校门的北大、清华学子送到了湖南西湖农场。整天劳动、批修、再劳动,又是“一年零九个月”,与他在北大学习的时间恰好吻合。之后(1972年岁尾)他被调到湖南省科委下面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又过了四年(1977年初),调去《新湘评论》,又过了两年多(1979年8月),他考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业是国际新闻。研究生毕业(1982年),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担任记者。后又下海任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再后又重返《人民日报》。
再往后呢?八十年代末,经历了一个多事之秋后,他的人生也亳无征兆突如其来地陷入了低潮。“我不知道自己从哪来,行将往哪儿去,更不知道,此时此刻身在何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
在这迷茫的时刻,他鬼使神差般地信步走进了北大,“母校,总有那无远弗届微末不弃的包容与厚泽”——这儿,是他精神的殿堂,灵魂的归宿。
仍然是“七拐八拐”,终于又回到了北大。
打这以后,只要工作上脱得开身,他就带上一本书,来到未名湖边,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一坐就是半天。回归燕园,成了他隔三差五的功课。
“我尝试着去蹭大教室的课。我斗胆去叩我敬仰的前贤大家的门。也就在那期间,我做了一个至今想想都莫名感动的决定,离开短暂的商海生涯,也离开原有的新闻轨道,从头开始学习,重新铸造人生。”人生的又一次归零,他第四次进入了“空杯状态”。
他自喻,这次回归北大是“读博”。没有指定的导师,没有规范的课程,纯粹属于自学。时间是从1989年秋,到1994年底,差不多也是“五年有半”。
“课程”的安排,起初是历史,中国的,外国的。接着是经济,重点跟踪几位大师,外国的,中国的。继而是人物传记,包括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由是又涉足自然科学,诸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量子力学等等。间或插入《易经》《堪舆学原理》《甲骨文字典》,以及一些内部出版的参考读物。不光是读书,他还去听课,书中就有他听课的记叙。他还旁及小说,新诗基本不看,他说没有找到对胃口的。散文也不看,他觉得小情小趣,提不起精神。“直到有一天——我记得清楚,是一九九四年十月,在济南——偶然读到台湾作家余光中的散文集《听听那冷雨》,惊诧,汉字原来可以这般排兵布阵。”
1995年春,他结束了五年的封闭自学,完成了他的“博士生”课程。
一双翅膀,又一次掠过未名湖面。一只载着哲思、认知,一只载着葳蕤文采、旺盛文气,飞越了现实红尘,飞向了群峰之颠,飞出了人生的大突围。翅膀划过之处,呈现出一道绚丽多姿的《岁月游虹》,全书七十七篇散文,季羡林老先生评价:“无论抒情,记事,或是说理,他的笔下常常有一种奇幻的光,与之相辅,艺术性强,文采葳蕤,颇具气韵、底蕴。”由此,他步入文坛。
此辑中《书斋浮想》《与我同行》《幸亏不是我》《生命是热烈跳动的音符》《假如有第二次生命》等文,篇篇闪烁着作者对世界、对人生的深邃思考,这种思考贯穿于接下来的四、五、六辑中北大人物的篇章。

肆
在接下来的三、四、五辑中,他写了“老五届”的北大,“涌立时代潮头”的北大,“先驱”的北大。
最令我捧读的是他写那些先驱、先贤。可谓是当年他踏入北大时,令他“目眩神迷”的那道光线的返照,折射出的是灵魂深处的对话,精神世界的漫游。
寻作者的笔墨,走进他的另一段北大的“步履途程”。
“博士生”毕业两年后,因一篇文章缘起,让他又撬开了北大的另一坨时间。
事由他那篇“煌煌上庠”而起。在北大一百周年校庆之际(1998年),他应邀撰文纪念,题目为“煌煌上庠”。为此,他搜集了海量资料,闭门阅读两月,然后又用了一两个月,将一千万字的阅读量,熔炼成一万字,铸成了这篇亦政论亦纪实亦抒情的散文。在《十月》1998年第一期刊发,反响非凡,杂志破格让他开设一个散文专栏“长歌当啸”,内容是管窥二十世纪的思想、文化大家,人物选由他确定。他事先没有想到的是,在回眸对二十世纪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时,无论怎样选择,都难绕开北大。
本书第五辑中收入的五篇文章,皆出于当年的《十月》专栏。
《煌煌上庠》里,蔡元培带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来到了北大。先是三顾茅庐,把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从上海接到北大,推到了时代舞台的前沿;随之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循踪而至;胡适身后,又迎来中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鲁迅也前来助阵,并同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联手,加入了《新青年》的营垒。也正是这个时间,毛泽东也来到这里,沉浸在沙滩红楼的图书馆中,可以肯定,正是北大,正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一批世纪人物的风采,开阔了青年毛泽东的视野,勃发了他“指点江山”的豪情,强化了他“到中流击水”的意志。
蔡元培,把中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先驱、思想先驱聚集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将一座旧北大改变成中国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策源地,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水到渠成地输送了大批思想、人力资源,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他带给北大最深的影响,蕴蓄着无限的精神财富。
前些天,看央视播出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总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今日又读卞毓方先生这篇二十年前的文章,顿时找到了这“相识”之处。原来,先生早就为这部电视剧写下了脚本的初稿。
在《梦灭浮槎》里,我看到的是这样的镜像:
波涛之中,胡适伫立“威尔逊总统号”后甲板上,这是他离开北大仓皇辞国之际。回望故国,黯然销魂。
书斋里,作者透过电脑荧屏,凝视着在太平洋胸脯上滑行的“威尔逊总统号”海轮,以及在后甲板凭栏怅望的胡适。
市声转沉,万籁趋寂,透过历史烟云,这是一场跨越了空间、穿越了时间的对视、沟通。
太平洋上,这位大力倡导白话文,为提倡“科学”与“民主”而不遗余力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总是想把命运之舵牢牢握在自己掌心的胡适,“东望不见启明,西望不见扶桑,南望不见仙岛,北望不见瑶光”,一番波涛浪涌之后,“想想此刻的自己,何尝不是一艘在风浪中颠来簸去、爬高跌下的海轮?而且舵握在别人的掌心。”
“胡适啊胡适,你究竟要到哪儿去,你究竟又能到哪儿去呢?——胡适喟然长叹。”
太平洋上的胡适在喟然长叹,书斋中的人在深深幽思:“假设时光倒流,让我们的胡博士重新做一次选择,他又有哪几条路好走呢?” 书斋中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地为他做了番推测:马寅初的路——他留在大陆的朋友、同事、学生已有示范,下场可推而测之。傅斯年的路——嗜好独裁专政的老蒋,又何尝能容忍胡大圣人的“民主” “自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陆这边“批胡炸胡”,台湾方面也发动了不点名的“剿胡”运动。由此而得:在第三条路上游走的胡适,无论在海峡的此岸和彼岸,都难有立足之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去香港,去第三国,注定是另一条颠沛流离之路。
此刻,书斋中人的思绪与“威尔逊总统号”上的胡适一起荡漾于海浪之中:“胡适的双脚,过早落向一个尚未出现的社会形态,这就如同在峡谷中荡秋千,永远上不扪高天,下不着实地。只有梦断浮槎!他拥抱新文化、新思想的激情,以及对民主与科学的深挚执着,仍然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所以,我相信,胡适即使诞生在未来的岁月,依然有可能充当一代继往开来、有为有守的学术大师。”
“那么,胡适或许就只有求救于高科技,把自己冷冻起来,等到下个世纪再解冻出山。”
胡适是听不到这一番跨越时空的议论了。但后来怎样了?书斋中人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道:这位民国史上“我的朋友胡适之”,经过那番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后,如今依然在民间的书架上广结善缘,在历史的烟霞里讲学论道。
《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塑”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第一任校长马寅初,作者在这尊“塑像”刻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思想领先百家,超越时代,注定要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常常要等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为后来者逐渐认识、接纳。” 马寅初与他的《新人口论》正是这种思想者的演绎。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已经超过六亿。马寅初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在1955年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首次就人口问题发言,引来公众质疑。1957年,马寅初把他的《新人口论》正式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按当时人口增长速度,他预测十五年后(1972年)将达八亿,五十年后(2007年)将达十六亿。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他被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批倒批臭。
时间,如同一块试金石,验证着他的“大逆”和“不道”。我搜索了一下相关资料,还没到马寅初预测的“十五年后”,1970年中国人口已达八亿……到1982年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我国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时,人口已经超过十亿。这种人口发展趋势,是一个农业大囯难以应对的。从五七年提出《新人口论》,到八二年被定为国策,他的理论历经二十五年的验证,终被后来者认识、接纳。还有,他当年的主张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经过了三十六年的“只生一胎”政策后,到了2016年又改成了“二胎”政策。近日在网上看到,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了,又要出台“三孩”政策了。
文章中的“一个画面”和“一段誓言”刻下了这位思想者在那个寒冷岁月中的坚毅面目:画面中的马寅初九鼎大吕,震烁古今;誓言中的马寅初宁呜而死,不默而生!
《独秀的另类“文存”》,让我想起曾翻看过的《独秀文存》,里面存的是他1915年至1921年的论文、随感和通信,记录着这位先驱者的思想历程。最早出版于1922年上海亚东图书馆,今天仍然在一版再版着。
书中的这篇另类“文存”,存的是鲜为人知的,在陈独秀命运的影子映照下的他的子孙,以及他的“身后”之事。
陈独秀的那股气脉,在他子孙们身上生成了浩气盈胸的凛然、不甘沉沦的意志,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斗争岁月中,还是在“斜阳衔着滴血的哀伤”里,慷慨激昂,奋力抗争。
长子延年、次子乔年成为响当当的舍生忘死的革命家,“独秀一门”,“五大”出了三个中央委员,开“党史之精粹,典籍之传奇”。刑场上,延年昂首挺立,誓死不跪,竟让行刑的刽子手差点扑倒在地。转年,乔年又英勇就义。又一次瞒了母亲来沪为亲人收尸的长女玉莹,前不见老父身影,后又不知如何向老母交代,悲恨交加,急火攻心,竟一病殁于沪上。
三子松年,在父亲走出国民党监狱后,带着祖母、妻子和长女,来到他的身边,辗转定居四川江津,靠教书度日,苦熬艰辛,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带着祖母和父亲的灵柩举家迁回故里。
回到故里,松年不敢用“陈独秀”大名,取他父科考时的“陈乾生”立碑安葬。每到清明,尽量避开熟人耳目,偷偷地带上儿女祭拜。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连偷偷祭祀也被迫停止了。直到1979年,他才再次前往。
文中载:1981年,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为爷爷的若干历史遗留,径直上书中共中央,邓小平就其中提到的坟墓一节,做出陈独秀墓做为文物单位保护的批示。次年被当地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重修墓冢,重立墓碑。
作者在文末提到:墓碑“上面镌刻的,仍然是‘陈独秀之墓’五个孤单单的大字”。言有尽而意有余。
又经过了十几载春风秋雨,墓碑上那孤单单的五个大字,“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陈独秀先生之墓”——这位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争议,也是最具人格魅力的人物终于被盖了棺、定了论。原来的墓园,现在也开辟成“独秀园”,占地110亩,设有惊雷浮雕、石牌坊、柏林墓道、陈独秀铜像、新青年碑刻、纪念水塘、陈独秀纪念馆,被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前来拜谒、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也算独秀先生的另类“文存”吧。
《凝望那道横眉》,看到这标题,就能让人联想到鲁迅,联想起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诗句。
“鲁迅是什么?在我,首先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元气。《呐喊》是元气,《彷徨》是元气,《热风》也是元气。” 写鲁迅的文章太多了,作者这篇要如何写?带着这个“?”,我一字一句地读下去。
他从数月前在三亚即兴所作的《文坛卡拉OK》开篇,“兴”由他随身携带的《今文观止》而起。前有清人辑《古文观止》,集历代散文经典,今人做《今文观止》也该是汇集名家名篇。最让作者感兴趣的是,里面既收有鲁迅的文章,也收有当年与鲁迅论战对手的文章,各路英雄同场献技,亮出的都是“看家的本事”。这场才艺比拼的如何呢?作者取阳台外的景色作了番精彩的比喻:有的像翠竹临风,有的像溪清沙白,有的似闲云出岫,还有的宛如浪尖上高张的白帆。唯鲁迅的文章截然不同,像威风凛凛的铲土机,像隔着海湾传来的移山开道的隆隆巨炮,它也柔韧……它更浩荡……作者感叹:“前面提到的诸公大作无一篇不可以克隆。鲁迅的文章,仿其皮毛可以,却绝对不能克隆。归根结底,是你生命的水银柱无法上升到鲁迅的高度。”
接下来,作者将镜头移向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台“拨剑相向、生死你我”的大戏……硝烟散去,当事人也已纷纷仙去。平心静气,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地去“对照了看”,相比之下:“元气就是元气,虚火就是虚火。”
鲁迅之子周海婴家的客厅里,就在作者凝望鲁迅画像的瞬间,那道横眉赐予了作者“一道灵光”:在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鲁迅?不是他的门生,不是他的亲友,也不是他的追随者、崇拜者,而是他的对手。
他的对手是谁?这一刹那,如同鲁迅当年翻阅历史,最终从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吃人”二字一样,让作者在鲁迅的那道横眉中读出他的真正对手是“黑喑”二字:“鲁迅毕生仇恨最烈、用力最专、下手最辣的,却是绵亘数千年的黑暗,是被黑暗同化了的‘奴性集体无意识’,以及麻木怯懦的‘看客’心理……唯‘黑暗’心知肚明,天下最希望鲁迅文章速朽的,不是别个,正是鲁迅他自己”。
在历史冷藏的具有经典价值的时髦派大师中,作者特别挑出了两个与鲁迅相关的在这里来写。一位是郭沫若,另一位是海峡彼岸的苏雪林。末了,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自马路对面,有鲜衣靓服的母女,款款进入我的视线。我无心中朝她俩多瞧了几眼,从审美的角度看,女儿无疑是优点的放大,母亲则是优点的缩小;从审丑的角度看,女儿无疑是缺点的缩小,母亲则是缺点的放大。——年龄的差异竟有这般敏感,世事不也正是如此吗?”
文中最后一节中:如果鲁迅活着,会是怎样?最后一段里:文学可以假设,而历史只承认实录。其实,文章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随着文章的结束,读此文前心中的那个“?”化成了“!”——感叹于作者独具的慧眼,和他那独具的匠心。

伍
有了《十月》名刊的连载,有了出版社的约稿,加之季羡林先生所言的“肯下苦功,惨淡经营”,《长歌当啸》一书横空出世,气贯长虹。其后,书中的部分篇目被陆续选入教材或进入高考试卷。
他说:“写作《长歌当啸》时,奠定了一种路数,即:大胆把小说、影视、政论的手法引进散文,也就是‘破体’;融记者的敏感、学者的宏识、诗人的激情于一炉,是则为风格。” 这种“破体”、“风格”,该是他长期思索后的立题和破题:“五四开始了白话文,现在有一条宽广的大路可奔,文章如何超越前代,这是摆在今人面前的课题。”
他说:“人生总处在寻找的过程。我从《长歌当啸》找起,到《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到《浪花有脚》,到《寻找大师》,再到《日本人的“真面目”》《美东+加勒比履痕》等等,手头在写的是日本的全部诺奖获得者,从国内找到国外,脚步一直未停。” 在寻找的途程中,他“破体”依旧,又增加了纪实的手法。
他著文,既着眼当前“画眉深浅入时无” ——于时代,于作家的良知和义务;更加放眼五十年后——他说五十年是约数,文章要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未来依然葆有强劲的生命力。这方面,从近年来他的文章越来越多地被编进大中学教材这一点上,起码已经通过了二十几年的考验了。再往后,该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去见证了。看“当当”网上一位书友留言:“卞毓方先生作品皆是经典。放眼五十年后,相信还能检验出足够的生命力。” 他相信,我也相信——卞毓方先生的文章会葆有这种强劲的生命力!
季羡林先生说到他的这位及门弟子:“毓方之所以肯下苦功夫,惨淡经营而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他腹笥充盈,对中国的诗文阅读极广,又兼浩气盈胸,见识卓荦;此外,他还有一个作家所必须具有的灵感。”
何健明先生也曾撰文《文道独行必大侠》评论他眼中的卞毓方:“卞毓方的散文作品我称之是‘知性’散文,即在完成常态的写情写景之上的那种融入知识与智慧的文学。”“我们的学者和学界,需要卞毓方这样的独行者,这样中国的文事才能彰显更加灿烂的光芒。”
纵观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无不是以其独特的视角、独立的思维,独具的笔法,从多维的角度慎思历史帷幕背后的真实,冷静思考现实问题的积疑,给人以反思、以启示。即使是论说政治和政治人物,笔端所及之处也不生硬、不胆怯、不回避,或直抒胸臆,或意在言外。就是意在言外,也能入木三分。他笔下类似的这种“直抒”和“言外”,如四溅的火花,不时地闪烁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之中。
近有学者读《北大与时间之外》评论:融哲学、美学、文学于一体,思绪万里,蕴涵丰富,视角独特,浓烈的北大情怀洋溢于字里行间,显现出崇高的精神与艺术境界。又见读者评:“卞毓方老师的散文、杂文、随笔,篇篇都是有主题、有思想、有研究、有根有据的。青年人读他的文章,会开觉、会顿悟、会终生受益。”这位读者的体会不可谓不深、不透。
合卷、闭目、仰思。脑海里浮现出他当年踏上北大校园的镜像:仿佛仰脸对了晌午的太阳,目眩神迷。读卞毓方先生,我又何尝不是登上了一座集文学、思想、行动之“煌煌上庠”,令人“目眩神迷”。
恍惚中,见“北冥有鱼,化而为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展翼,划出文化之大气象、精神之大格局;拢羽,抖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元气始然。一望而知,是从未名湖畔上空掠过的。

作者简介

路远明,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协会员,中国石油作协会员。散文集《从森林到草原》获第四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散文《塔里木墙上的大表》获第三届“华夏散文奖·精锐奖”,散文《坐饮香茶爱此山》获首届“羡林杯”生态散文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