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奇人,丰神不朽。每每读到那些卓然不群的历史人物,总有一种穿越时空、直击灵魂的震撼。此次拜读《人物》杂志上发表的《奇人朱复戡》的长文,感慨尤深。文章从沙孟海先生讲述的“日本人认不出他是谁”的趣事引入,从朱复戡先生的姓名之变谈到学术之严、生活之逸,再到为人为艺的逸闻趣事,一桩桩、一件件娓娓道来,将其才情之深、性情之真,展现得淋漓尽致、清晰可触。原来所谓“奇人”,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之卓越,更在于其人格之丰厚、生活之独特、气质之洒脱,朱复戡就是这样一位“真性情的大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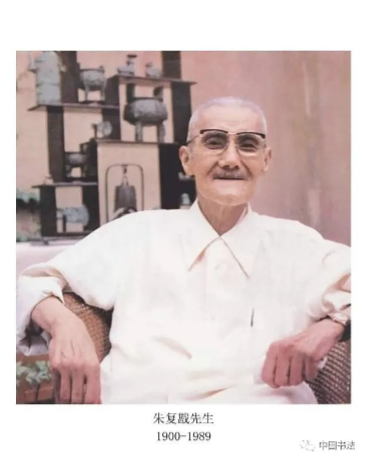
文中对先生姓名更迭之考究与趣谈着实令人莞尔,从中我们也可窥得这位“神童”的任性与自在。先生一生更名几十次,从乳名阿兰、学名义方,到后来的复戡、公陶、紫阳、赤子,乃至各种笔名、号、别署,如静龛、秦戡、博尹、朱振邦……这些名字有的出于意趣、有的寄托志趣、有的藏着谐音玄机,可似乎都在传递一个信息:他对“名”的态度并不执着,反倒是随性自然、一派天真。然而这位对“名”极端轻视的才子,对“艺”却极端重视,甚至视“艺”如命根。马公愚评他“于名信手拈舍,于利随挥去来”,老子言“以无名为名”,在朱复戡身上竟得了活现。他的这一态度,令人不禁反思当下许多艺术创作者热衷“出圈”“走红”的功利心——名不一定来自真正的才华,也未必配得上真正的艺术,而朱复戡,则是将“真名”藏在了“无名”之后。
张大千曾言朱复戡“懒散成性”,刘海粟也评其“做学问极精道,做人太懒散”,这或许正是这位“奇人”最有意思的一点。表面看,他似乎任性不羁,不守常规,上课迟到,甚至为了跳舞而旷课;但细读文章,我们发现他在艺术上的“懒散”其实是一种有选择的洒脱,是对庸常制度的抗拒,而不是对艺术本身的敷衍。
最令人动容的是那段“包饼”故事。他用包饼教学生包美术的“美”——将一块饼用纸包得工整如艺术品,寓言美学之细微、美术之道,从生活中显现修养。从小处见真章,从“包饼”到“钤印”,从“唱腔”到“写字”,无不体现出他对细节的极致讲究,对艺术形式与精神的双重敬畏。这种人生态度,也许正是“精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他懒,是对制度的厌倦;他精,是对艺术的虔诚。这样的“懒”与“精”并存,令他的人格更显丰满,也更接近一个“真”字。
朱复戡的“精道”不仅体现在讲学、作画,更体现在对细节的锱铢必较之中。文章中提到他因不放心学生钤印,竟将学生的印章“扣留”在自己处。他的“差一点都不行”,并非吹毛求疵,而是一种艺术家的终极执念。
文章讲到吴昌硕训子的一则故事。吴迈钤印失误,只差一点点,便被父亲当众一耳光训斥,连朱复戡都劝吴老“何必如此”,却遭吴昌硕怒斥:“朱义方都能看出你不行!”此段将“差一点”的重要性凸显得入木三分。这种执着,是传统文人对“规矩”的坚守,是艺术家对“境界”的要求,更是师长对“传承”的负责。
朱复戡正是这样一位“传承有道”的先生,他用最生活化的方式,如包饼、唱腔、钤印、作画,一点一滴灌输“艺术不能差一点”的理念,虽琐碎,然真诚而坚定。
文章写他在法国学画重写实,回国后依然关心翎毛兽足之细节——这是对绘画基本功的尊重,也是对西学精髓的吸收。在这点上,朱复戡兼具东方文人的儒雅与西方艺术家的精准。他不是只会写诗、刻印、写字的“书斋才子”,他同样懂形体、解结构、习技艺。这种东西融合的气质,也正是20世纪中国文人艺术转型期的缩影。
他玩车玩枪、与梅兰芳同为“美男子”,出入青帮、结识大亨,既疏狂又锋利。他的“赤兔马”曾为蒋宋婚车,他的“炼银枪”则差点让他入狱,世俗生活与风雅情趣交织在他身上,丝毫不显突兀,反而浑然天成。这正是“奇人”的魅力所在:既有风流浪子之不羁,又有治艺如命之庄严;既涉人间烟火,又修精神至境。
文章后半部分提到,今人多知朱复戡的篆刻书法,可知其绘画者少,知其诗文者更少,而几乎无人知其“才思敏捷”,精于文物鉴定,深谙青铜器造型、纹饰、文字研究,更别说知其会武术、还是京剧余派老生的名票等等。这让人很是慨叹:先生在“神童”光环与“四绝”名头之后,竟还有如此傲人的“盲区”。果然,真正的奇人,往往把最锋利的才华藏于不经意之间,不为炫技,只为自娱或他娱。
文章中提及他为孙雪泥设计信笺,抓住“飞鸿延年”与“生生”二字组合,意象精妙;为包兆龙图书馆写碑文,以三种碑体糅而书成“龙”之意象;为张大千刻印“张爰、大利、千万”,既含名字、字号,又寓吉祥如意,且纵横可读,多义巧构。这种创意不是装腔作势的标新立异,而是学识、趣味、功底与时代感的综合体现,足见“奇人”之不拘一格。
尤让我击节赞叹的,是他为玉佛寺真禅法师所作的嵌字联:“千方丹顶皈禅寺,万丈菩提依真身”,不仅嵌入法号“真禅”,还隐含其俗名“鹤树”,一联之中三重嵌名,字字合情,句句得意,真正是才思灵动、技艺娴熟、表达含蓄。这不是哗众取宠的“玩文字游戏”,而是对传统文化入骨三分的通达与创造。当下很多人玩“嵌名”“藏字”,但多为噱头,浮于表面,朱复戡却能将嵌字联写得既有意境、又有情感,还不乏禅意,堪称“藏锋不露”的典范。
文章不仅描绘了朱复戡的个性、艺术与趣事,更让我感受到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一方面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却又精妙契合。他既是传统文化的传人——书法、篆刻、诗文皆得晋唐宋元之气,又是新文化与西方艺术的受益者——游学法国,画油画、开红车、玩洋枪、跳交谊舞。这种“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的身份,使得他既能在美专吸引满堂学生,又能在法租界涉险脱身。既能与张大千、梅兰芳等交游唱和,又能避开政治中心,守住学术与艺术的尊严。
他的“时代错位”,在于他未曾完全顺从体制,也从未迎合潮流。他不主动争名夺利,却常因才华被时代“请出山”;他不居庙堂高位,却始终被艺术圈尊为“先生”“高人”;他不为世俗生活妥协,却在不经意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学人。而他的“时代合拍”,则体现在他对新知的拥抱、对多元的接受——从鹰拳到油画、从戏曲到篆刻,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跨文化的流动。他的存在,如同一道桥梁,沟通传统与现代、中西与本土。
朱复戡的身上,聚合了近现代中国文人身上最独特也最珍贵的几种品质:
首先,是“自由不羁”的个性。他敢于弃名利于不顾,敢于为跳舞不上课,敢于“名字随心改”,敢于“打扮得比梅兰芳还美”。这不是矫饰,而是内心自由的自然流露。
其次,是“严谨入微”的治学态度。从包饼到钤印、从作画到嵌联,凡事都一丝不苟、力求尽善。他知道,“差一点”的宽容是艺术死亡的开始。
再次,是“通才兼备”的博学风采。他不是“精专一艺”的工匠型艺术家,而是融诗、书、画、印、武术、戏曲、青铜文物、西洋艺术于一炉的“士大夫式艺术家”。他的艺术,是一种精神通达之后的自然外化,是一种生活审美的整体流露。
最后,是“真诚厚道”的为人之道。他择人三不交:心术不正者不交、技艺平庸者不交、面目可憎者不交。标准虽严,却体现他对“人品”与“艺品”的双重敬重。他收徒看“面相”,送饼不忘“美感”,严师慈父、率性而为,皆可爱可敬。
在当下“娱乐化”逐渐侵蚀“文人”本质的环境氛围中,朱复戡这样的形象如一泓清泉,让人想起那个时代还有这样一群人,以才华和风骨立世,以风趣和自由生活。他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却是真真正正的“文人”。
读完文章,不禁发问:今天的我们,还能拥有这样的“奇人”吗?在一个媒介洪流裹挟、短视频爆炸、流量为王的时代,这种“淡泊名利而自成高格”的风骨几乎成了稀有物种。许多所谓“文化人”忙着直播卖字画、蹭热点、争出圈,少有人能像朱复戡一样,几十年沉在学问、技艺与生活里,做学问不为炫耀,养性情不为人设。朱复戡之“奇”,不是怪异而是稀缺;他的“自由”,不是放纵而是脱俗;他的“懒散”,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对庸常规训的抗拒。更难得的是,他那种“以细节见精神”的严谨,那种“将艺术之美内化为生活之美”的态度,才是“真才实学、风骨自由”的文人之道,堪为我辈勉励践行之典范。一位朱复戡,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文艺理想。
品读《奇人朱复戡》,不仅是趣味横生的文化漫游,更是一场对艺术与人格的精神洗礼。朱复戡之“奇”,不在于离经叛道,而在于他将“做自己”与“成大家”的完美统一。他是一个真实的传说,一个生动的文化符号,一个我们当代极度稀缺的“文人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