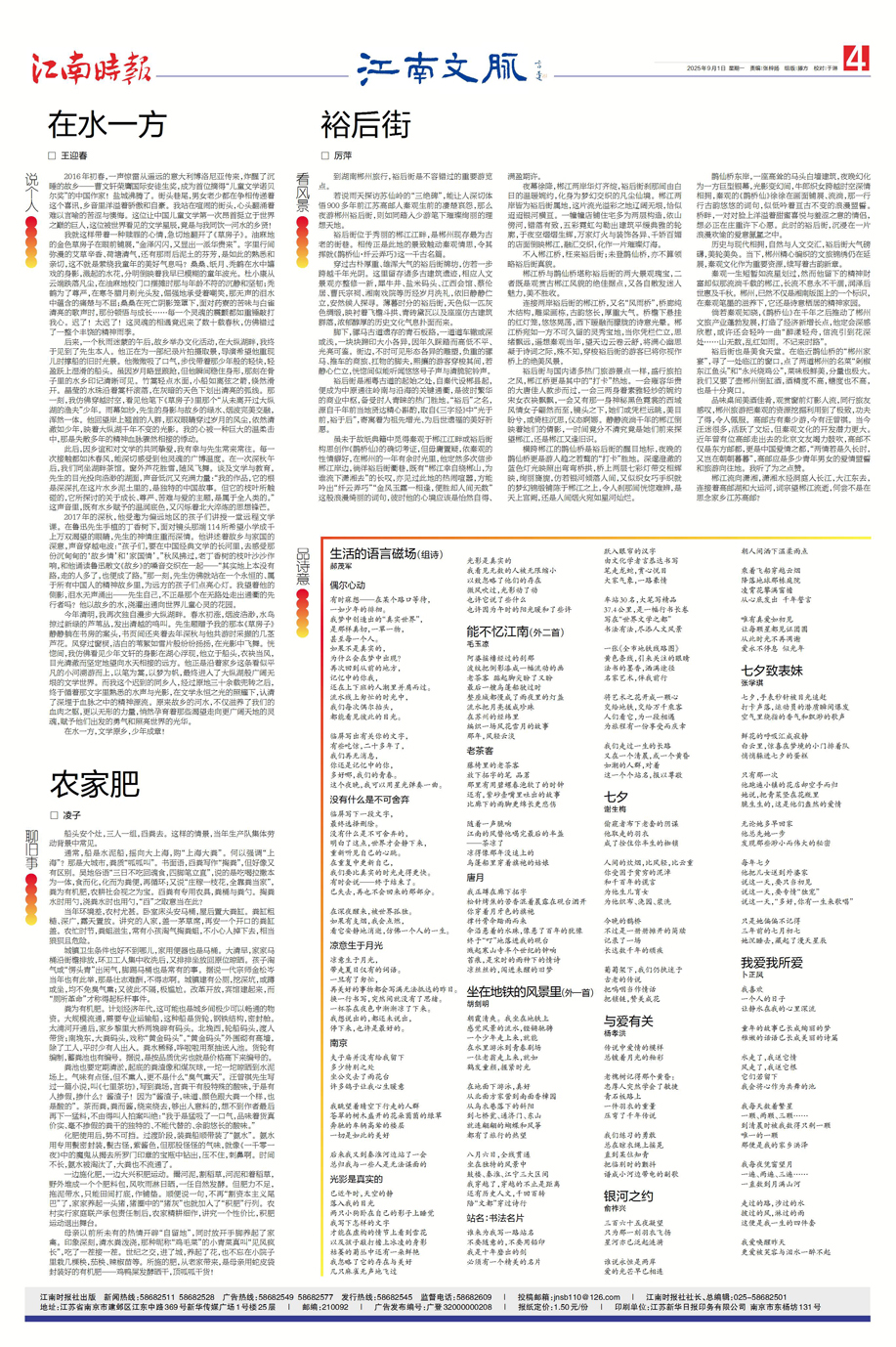在水一方
□ 王迎春
2016年初春,一声惊雷从遥远的意大利博洛尼亚传来,炸醒了沉睡的故乡——曹文轩荣膺国际安徒生奖,成为首位摘得“儿童文学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盐城沸腾了。街头巷尾,男女老少都在争相传递着这个喜讯,乡音里洋溢着骄傲和自豪。我站在喧闹的街头,心头翻涌着难以言喻的苦涩与懊悔。这位让中国儿童文学第一次昂首挺立于世界之巅的巨人,这位被世界看见的文学星辰,竟是与我同饮一河水的乡贤!
我就这样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情,急切地翻开了《草房子》。油麻地的金色草房子在眼前铺展,“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字里行间弥漫的艾草辛香、荷塘清气,还有那雨后泥土的芬芳,是如此的熟悉和亲切,这不就是萦绕我童年的美好气息吗?桑桑、纸月、秃鹤在水中嬉戏的身影,溅起的水花,分明倒映着我早已模糊的童年波光。杜小康从云端跌落凡尘,在油麻地校门口摆摊时那与年龄不符的沉静和坚韧;秃鹤为了尊严,在寒冬腊月剃光头发,倔强地承受着嘲笑,那无声的泪水中蕴含的痛楚与不屈;桑桑在死亡阴影笼罩下,面对药寮的苦味与白雀清亮的歌声时,那份顿悟与成长……每一个灵魂的震颤都如重锤敲打我心。迟了!太迟了!这灵魂的相遇竟迟来了数十载春秋,仿佛错过了一整个丰饶的精神雨季。
后来,一个秋雨迷蒙的午后,故乡举办文化活动,在大纵湖畔,我终于见到了先生本人。他正在为一部纪录片拍摄取景,导演希望他重现儿时撑船的旧时光景。他微微吸了口气,步伐带着那少年般的轻快,轻盈跃上湿滑的船头。虽因岁月略显踉跄,但他瞬间稳住身形,那刻在骨子里的水乡印记清晰可见。竹篙轻点水面,小船如离弦之箭,倏然滑开。晶莹的水珠沿着篙杆滚落,在灰暗的天色下划出清亮的弧线。那一刻,我仿佛穿越时空,看见他笔下《草房子》里那个“从未离开过大纵湖的渔夫”少年。雨幕如纱,先生的身影与故乡的绿水、烟波完美交融,浑然一体。他回望岸上翘首的人群,那双眼睛穿过岁月的风尘,依然清澈如少年,映着大纵湖千年不变的光影。我的心被一种巨大的温柔击中,那是失散多年的精神血脉骤然相接的悸动。
此后,因乡谊和对文学的共同挚爱,我有幸与先生常来常往。每一次接触都如沐春风,能深切感受到他灵魂的广博温度。在一次深秋午后,我们同坐湖畔茶馆。窗外芦花胜雪,随风飞舞。谈及文学与教育,先生的目光投向浩渺的湖面,声音低沉又充满力量:“我的作品,它的根是深深扎在这片水乡泥土里的,是独特的中国故事。但它的枝叶所触碰的,它所探讨的关于成长、尊严、苦难与爱的主题,是属于全人类的。”这声音里,既有水乡赋予的温润底色,又闪烁着北大淬炼的思想锋芒。
2017年的深秋,他受邀为偏远地区的孩子们讲授一堂远程文学课。在鲁迅先生手植的丁香树下,面对镜头那端114所希望小学成千上万双渴望的眼睛,先生的神情庄重而深情。他讲述着故乡与家国的深意,声音穿越电波:“孩子们,要在中国经典文学的长河里,去感受那份沉甸甸的‘故乡情’和‘家国情’。”秋风拂过,老丁香树的枝叶沙沙作响,和他诵读鲁迅散文《故乡》的嗓音交织在一起——“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一刻,先生仿佛就站在一个永恒的、属于所有中国人的精神故乡里,为远方的孩子们点亮心灯。我望着他的侧影,泪水无声涌出——先生自己,不正是那个在无路处走出通衢的先行者吗?他以故乡的水,浇灌出通向世界儿童心灵的花园。
今年清明,我再次独自漫步大纵湖畔。春水初涨,烟波浩渺,水鸟掠过新绿的芦苇丛,发出清越的鸣叫。先生题赠予我的那本《草房子》静静躺在书房的案头,书页间还夹着去年深秋与他共游时采撷的几茎芦花。风穿过窗棂,洁白的苇絮如雪片般纷纷扬扬,在光影中飞舞。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少年文轩的身影在湖心浮现,他立于船头,衣袂当风,目光清澈而坚定地望向水天相接的远方。他正是沿着家乡这条看似平凡的小河溯游而上,以笔为篙,以梦为帆,最终进入了大纵湖般广阔无垠的文学世界。而我这个迟到的同乡人,经过原地三十余载兜转之后,终于循着那文字里熟悉的水声与光影,在文学永恒之光的照耀下,认清了深埋于血脉之中的精神源流。原来故乡的河水,不仅滋养了我们的血肉之躯,更以无形的力量,悄然孕育着那些渴望走向更广阔天地的灵魂,赋予他们出发的勇气和照亮世界的光华。
在水一方,文学原乡,少年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