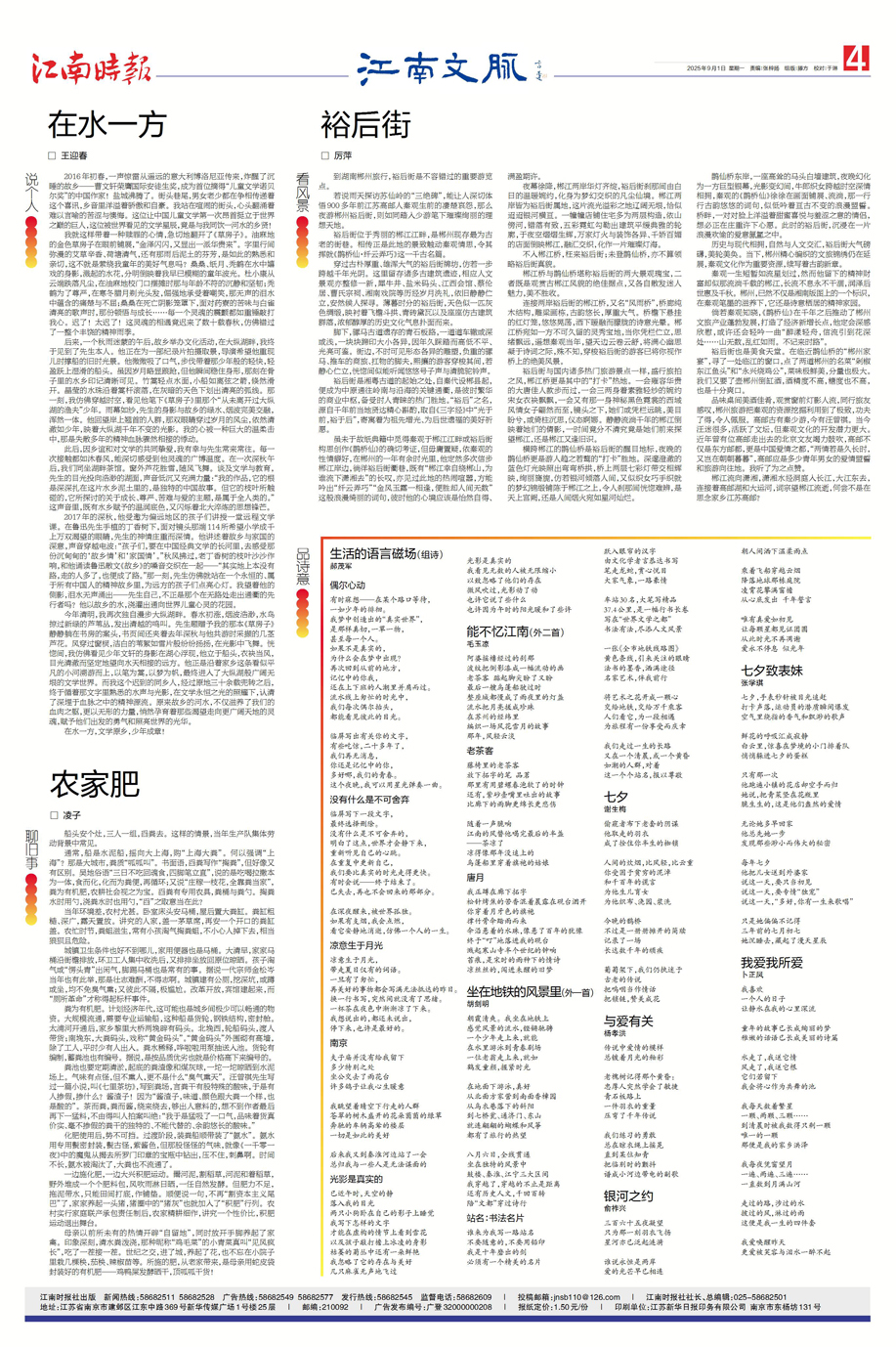农家肥
□ 凌子
船头安个灶,三人一组,舀粪去。这样的情景,当年生产队集体劳动背景中常见。
通常,船是水泥船,摇向大上海,购“上海大粪”。何以强调“上海”?那是大城市,粪质“呱呱叫”。书面语,舀粪写作“掏粪”,但好像又有区别。吴地俗语“三日不吃回魂食,四脚笔立直”,说的是吃喝拉撒本为一体,食而化,化而为粪便,再循环;又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粪为有机肥,农耕社会视之为宝。舀粪有专用农具,粪桶与粪勺。掏粪水时用勺,浇粪水时也用勺,“舀”之取意当在此?
当年环境差,农村尤甚。卧室床头安马桶,屋后置大粪缸。粪缸粗糙、深广,露天置放。讲究的人家,盖一茅草席,再安一个开口的粪缸盖。农忙时节,粪蛆滋生,常有小孩淘气掏粪蛆,不小心人掉下去,相当狼狈且危险。
城镇卫生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家用便器也是马桶。大清早,家家马桶沿街檐排放,环卫工人集中收洗后,又排排坐放回原位晾晒。孩子淘气或“愣头青”出闲气,脚踢马桶也是常有的事。据说一代宗师金松岑当年也有此举,那是壮志难酬,不得志啊。城镇建有公厕,挖深坑,或蹲或坐,均不免臭气熏;又彼此不隔,极尴尬。改革开放,宾馆建起来,而“厕所革命”才称得起标杆事件。
粪为有机肥。计划经济年代,这可能也是城乡间极少可以畅通的物资。大规模流通,需要专业运输船,这种船是货轮,钢铁结构,密封舱。太浦河开通后,家乡黎里大桥两堍辟有码头。北堍西,轮船码头,渡人带货;南堍东,大粪码头,戏称“黄金码头”。“黄金码头”外围砌有高墙,除了工人,平时少有人出入。粪水稀释,哗啦啦用泵抽送入池。货轮有编制,蓄粪池也有编号。据说,是按品质优劣也就是价格高下来编号的。
粪池也要定期清淤,起底的粪渣像和煤灰球,一坨一坨晾晒到水泥场上。气味有点怪,但不熏人,更不是什么“臭气熏天”。汪曾祺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叫《七里茶坊》,写到粪场,言粪干有股特殊的酸味,于是有人掺假,掺什么?酱渣子!因为“酱渣子,味道、颜色跟大粪一个样,也是酸的”。茶而粪,粪而酱,绕来绕去,够出人意料的,想不到作者最后再下一猛料,不由得叫人拍案叫绝:“我于是猛吸了一口气,品味着货真价实、毫不掺假的粪干的独特的、不能代替的、余韵悠长的酸味。”
化肥使用后,势不可挡。过渡阶段,装粪船顺带装了“氨水”。氨水用专用甏密封装,甏古怪,紫酱色,但那股怪怪的气味,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魔鬼从揭去所罗门印章的宝瓶中钻出,压不住,刺鼻啊。时间不长,氨水被淘汰了,大粪也不流通了。
一边施化肥,一边大兴积肥运动。罱河泥,割稻草,河泥和着稻草,野外堆成一个个肥料包,风吹雨淋日晒,一任自然发酵。但肥力不足,拖泥带水,只能田间打底,作铺垫。顺便说一句,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家家养起一头猪,猪圈中的“猪灰”也就加入了“积肥”行列。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家精耕细作,讲究一个性价比,积肥运动退出舞台。
母亲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辟“自留地”,同时放开手脚养起了家禽。印象深刻,清水粪泼浇,那种昵称“鸡毛菜”的小青菜真叫“见风疯长”,吃了一茬接一茬。世纪之交,进了城,养起了花,也不忘在小院子里栽几棵秧,茄秧、辣椒苗等。所施的肥,从老家带来,是母亲用蛇皮袋封装好的有机肥——鸡鸭屎发酵晒干,顶呱呱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