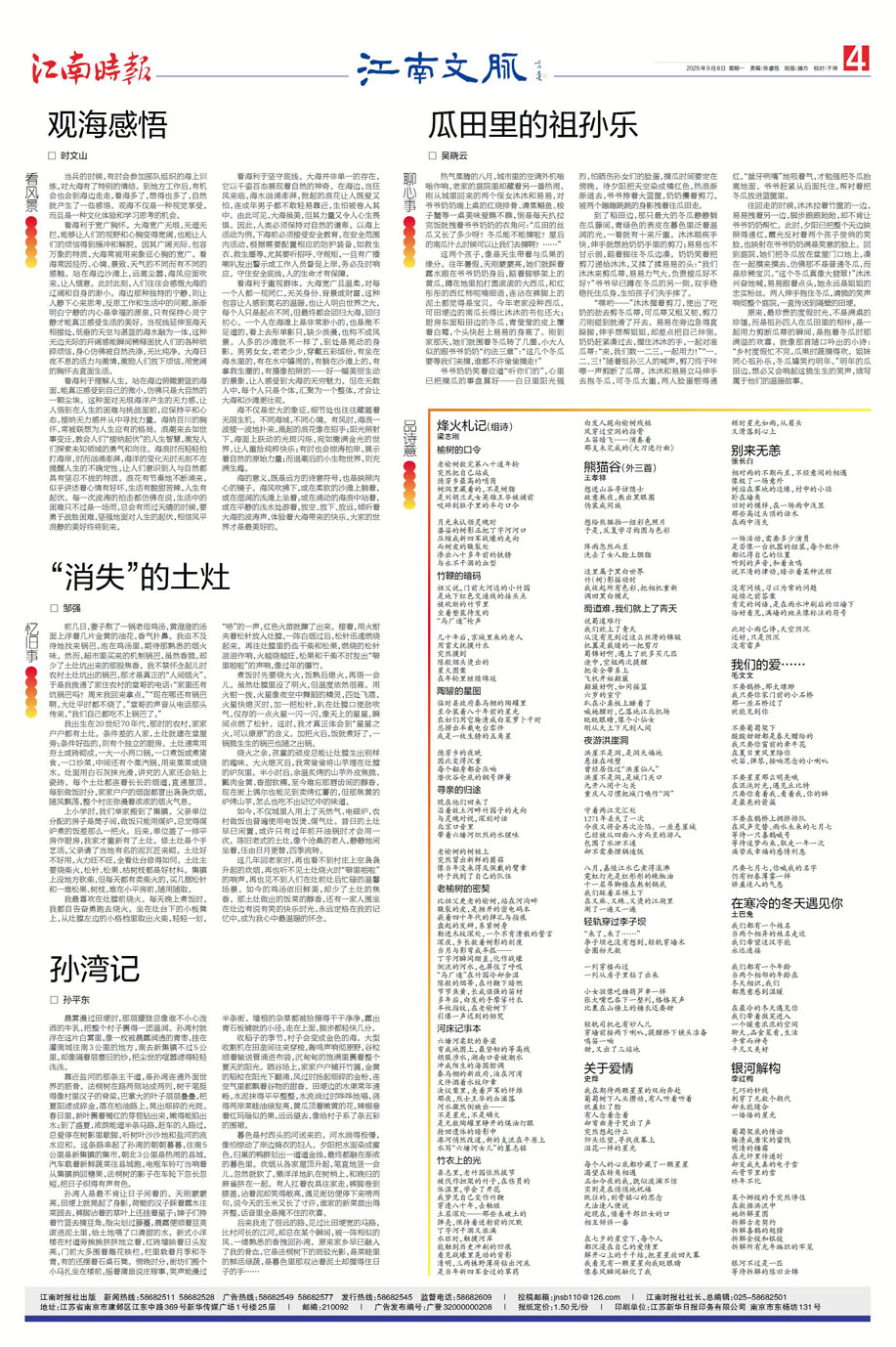“消失”的土灶
□ 邹强
前几日,妻子熬了一锅老母鸡汤,黄澄澄的汤面上浮着几片金黄的油花,香气扑鼻。我迫不及待地找来锅巴,泡在鸡汤里,期待那熟悉的烟火味。然而,超市里买来的机制锅巴,虽然香脆,却少了土灶炕出来的那股焦香。我不禁怀念起儿时农村土灶炕出的锅巴,那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于是我拨通了家住农村的堂哥的电话:“家里还有炕锅巴吗?周末我回来拿点。”“现在哪还有锅巴啊,大灶平时都不烧了。”堂哥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我们自己都吃不上锅巴了。”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土灶。条件差的人家,土灶就建在堂屋旁;条件好些的,则有个独立的厨房。土灶通常用夯土或砖砌成,一大一小两口锅,一口煮饭或煮猪食,一口炒菜,中间还有个蒸汽锅,用来蒸菜或烧水。灶面用白石灰抹光滑,讲究的人家还会贴上瓷砖。每个土灶都连着长长的烟道,直通屋顶。每到做饭时分,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出袅袅炊烟,随风飘荡,整个村庄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息。
上小学时,我们举家搬到了集镇。父亲单位分配的房子是筒子间,做饭只能用煤炉,总觉得煤炉煮的饭差那么一把火。后来,单位盖了一排平房作厨房,我家才重新有了土灶。修土灶是个手艺活,父亲请了当地有名的泥瓦匠来砌。土灶好不好用,火力旺不旺,全看灶台修得如何。土灶主要烧柴火,松针、松果、枯树枝都是好材料。集镇上没地方砍柴,但每天都有卖柴火的,买几捆松针和一堆松果、树枝,堆在小平房前,随用随取。
我最喜欢在灶膛前烧火。每天晚上煮饭时,我都自告奋勇跑去烧火。坐在灶台下的小板凳上,从灶膛左边的小格档里取出火柴,轻轻一划,“哧”的一声,红色火苗就蹿了出来。接着,用火钳夹着松针放入灶膛,一阵白烟过后,松针迅速燃烧起来。再往灶膛里扔些干柴和松果,燃烧的松针滋滋作响,火越烧越旺,松果和干柴不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过年的爆竹。
煮饭时先要烧大火,饭熟后熄火,再焐一会儿。虽然灶膛里没了明火,但温度依然很高。用火钳一拨,火星像夜空中舞蹈的精灵,四处飞落。火星快熄灭时,加一把松针,趴在灶膛口使劲吹气,仅存的一点火星一闪一闪,像天上的星星,瞬间点燃了松针。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含义。加把火后,饭就煮好了,一锅脆生生的锅巴也随之出锅。
烧火之余,孩童的顽皮总能让灶膛生出别样的趣味。大火熄灭后,我常偷偷将山芋埋在灶膛的炉灰里。半小时后,余温炙烤的山芋外皮焦脆、瓤肉金黄、香甜软糯,至今难忘那唇齿间的醇香。现在街上偶尔也能见到卖烤红薯的,但那焦黄的炉烤山芋,怎么也吃不出记忆中的味道。
如今,不仅城里人用上了天然气、电磁炉,农村做饭也普遍使用电饭煲、煤气灶。昔日的土灶早已闲置,或许只有过年前开油锅时才会用一次。陈旧老式的土灶,像个沧桑的老人,静静地闲坐着,任由日月更替,四季流转。
这几年回老家时,再也看不到村庄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再也听不见土灶烧火时“噼里啪啦”的响声,再也见不到人们在灶前灶后忙碌的温馨场景。如今的鸡汤依旧鲜美,却少了土灶的焦香。那土灶做出的饭菜的醇香,还有一家人围坐在灶边有说有笑的快乐时光,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心中最温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