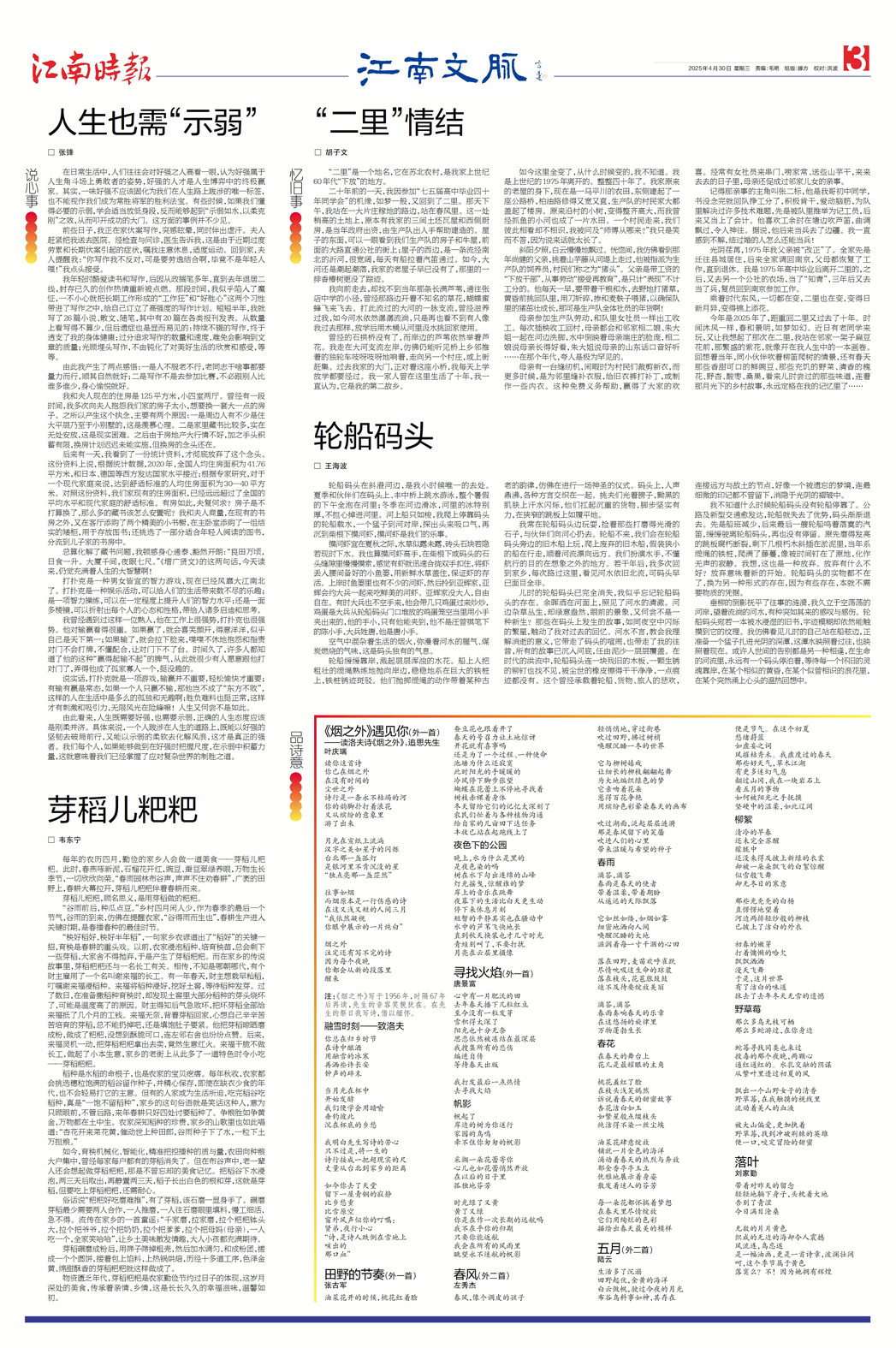“二里”情结
□ 胡子文
“二里”是一个地名,它在苏北农村,是我家上世纪60年代“下放”的地方。
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因参加“七五届高中毕业四十年同学会”的机缘,如梦一般,又回到了二里。那天下午,我站在一大片庄稼地的路边,站在春风里。这一处稍高的土地上,原本有我家的三间土坯瓦屋和西侧厨房,是当年政府出资,由生产队出人手帮助建造的。屋子的东面,可以一眼看到我们生产队的房子和牛屋,前面的大路直通公社的街上;屋子的西边,是一条流经南北的沂河,很宽阔,每天有船拉着汽笛通过。如今,大河还是潮起潮落,我家的老屋子早已没有了,那里的一排香椿树更没了踪迹。
我向前走去,却找不到当年那条长满芦苇,通往张店中学的小径,曾经那路边开着不知名的草花,蝴蝶蜜蜂飞来飞去。打此流过的大河的一脉支流,曾经滋养过我,如今河水依然潺潺流淌,只是再也看不到有人像我过去那样,放学后用木桶从河里汲水挑回家使用。
曾经的石拱桥没有了,而岸边的芦苇依然举着芦花。我走在大河支流左岸,仿佛仍能听见桥上乡邻推着的独轮车吱呀吱呀地响着,走向另一个村庄,或上街赶集。过去我家的大门,正对着这座小桥,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我一家人曾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我一直认为,它是我的第二故乡。
如今这里全变了,从什么时候变的,我不知道。我是上世纪的1975年离开的。整整四十年了。我家原来的老屋的身下,现在是一马平川的农田,东侧建起了一座公路桥,柏油路修得又宽又直,生产队的村民家大都盖起了楼房。原来沿村的小树,变得整齐高大,而我曾经抓鱼的小河也成了一片水田。一个村民走来,我们彼此相看却不相识,我被问及“师傅从哪来?”我只是笑而不答,因为说来话就太长了。
斜阳夕照,白云慢慢地飘过。恍惚间,我仿佛看到那年尚健的父亲,挑着山芋藤从河堤上走过,他被指派为生产队的饲养员,村民们称之为“猪头”。父亲是带工资的“下放干部”,从事劳动“接受再教育”,是只计“表现”不计工分的。他每天一早,要带着干粮和水,去野地打猪草,黄昏前挑回队里,用刀斩碎,掺和麦麸子喂猪,以确保队里的猪茁壮成长,那可是生产队全体社员的年货啊!
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和队里女社员一样出工收工。每次插秧收工回村,母亲都会和邻家相二娘、朱大姐一起在河边洗脚,水中倒映着母亲端庄的脸庞,相二娘说母亲长得好看,朱大姐说母亲的山东话口音好听……在那个年代,夸人是极为罕见的。
母亲有一台缝纫机,闲暇时为村民们裁剪新衣,而更多时候,是为邻里缝补衣服,给旧衣裤打补丁,或制作一些内衣。这种免费义务帮助,赢得了大家的欢喜。经常有女社员来串门、唠家常、送些山芋干,来来去去的日子里,母亲还促成过邻家儿女的亲事。
记得那亲事的主角叫张二标,他是我哥初中同学,书没念完就回队挣工分了,积极肯干,爱动脑筋,为队里解决过许多技术难题,先是被队里推举为记工员,后来又当上了会计。他喜欢工余时在塘边吹芦笛,曲调飘过,令人神往。据说,他后来当兵去了边疆。我一直感到不解,结过婚的人怎么还能当兵!
光阴荏苒,1975年我父亲被“改正”了。全家先是迁往县城居住,后来全家调回南京,父母都恢复了工作,直到退休。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后离开二里的,之后,又去另一个公社的农场,当了“知青”,三年后又去当了兵,复员回到南京参加工作。
乘着时代东风,一切都在变,二里也在变,变得日新月异,变得锦上添花。
今年是2025年了,距重回二里又过去了十年。时间沐风一样,春和景明,如梦如幻。近日有老同学来玩,又让我想起了那次在二里,我站在邻家一架子扁豆花前,那繁盛的紫花,就像开在我人生中的一本画卷。回想着当年,同小伙伴吹着柳笛爬树的情景,还有春天那些香甜可口的鲜豌豆、那些充饥的野菜、清香的槐花、野杏、酸枣、桑果,看来儿时尝过的那些味道,连着那月光下的乡村故事,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