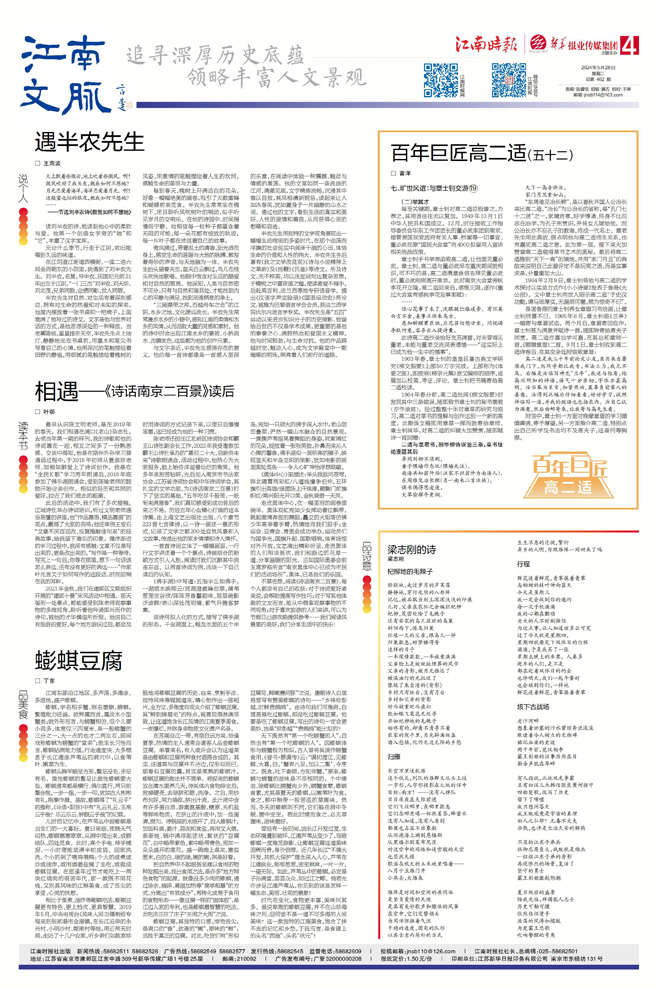蟛蜞豆腐
□ 丁东
江南东部沿江地区,多芦荡,多滩涂,多湿地,盛产蟛蜞。
蟛蜞,学名相手蟹,别名磨蜞、螃蜞,繁殖能力旺盛。就种属而言,属淡水小型蟹类;就外形而言,与螃蟹相仿,但个儿要小很多,体宽仅三四厘米,是一般螃蟹的三分之一,大一点的也才二两左右,民间戏称蟛蜞为螃蟹的“堂弟”;就生长习性而言,蟛蜞钻洞能力强,行走速度快,大多栖息于长江滩涂芦苇丛的洞穴中,以食苇叶、嫩草为生。
蟛蜞头胸甲略呈方形,螯足没毛,步足有毛。雄性蟛蜞的螯足比雌性蟛蜞要大些。蟛蜞通常都是横行,偶尔直行,两只前螯合抱,一步一摇,一步一叩,犹如古人彬彬有礼,抱拳作揖。是故,蟛蜞得了“礼云子”的雅称。《论语·阳货》中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记载。
儿时的记忆中,在芦苇丛中捉蟛蜞是后生们的一大喜好。夏日来临,夜晚天气闷热,蟛蜞窸窸窣窣,从洞中爬出来,成群结队,四处觅食。此时,亮个手电,伸手捕捉,一小时便能装满半蛇皮袋。回家洗洗,个小的剁了喂鸡喂鸭;个大的或煮或炒或油炸,或用酒姜盐腌了生吃,或做成蟛蜞豆腐。在那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两块红烧肉的艰苦年代,那一款既不用花钱,又别具风味的江鲜美食,成了舌尖的享受、心灵的抚慰。
相比于蒸煮、油炸等蟛蜞吃法,蟛蜞豆腐更有特色、更上档次、更具智慧。2019年5月,中央电视台《风味人间2》摄制组专程来到张家港市金港镇,在长江沿岸的永兴村、小明沙村、朝南村等地,用近两天时间,走访了十几户农家,听乡亲们如数家珍般地将蟛蜞豆腐的历史、由来、烹制手法、独特风味等娓娓道来,精心制作出一部短片,全方位、多角度向观众介绍了蟛蜞豆腐。其“鲜到掉眉毛”的特点,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这道饱含长江风情的江南夏季美食,一夜爆红,并跻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苏南沿江一带,有朋自远方来,恰逢夏季,热情的主人通常会请客人品尝蟛蜞豆腐。单看菜名,有人或许会以为这道菜是由蟛蜞和豆腐两种食材混搭合成的。其实,这道菜与豆腐并不沾边,仅形似而已。那看似豆腐的羹,其实是蒸熟的蟛蜞汁。蟛蜞豆腐的做法并不简单。将捉来的蟛蜞放在清水里养几天,待其体内食物排空后,掀掉硬壳,去除脐和腮,洗净。之后,用纱布包好,用力捣碎,挤出汁液。此汁液中含有许多蛋白质、游离氨基酸、糖原、无机盐等鲜味物质。在挤出的汁液中,加一些蛋清,搅匀。待锅里的水烧开了,舀入蟛蜞汁,加些料酒、姜汁、蒜泥和食盐,再用文火煨。渐渐地,锅中沸浮起团状、絮状的“豆腐花”,白中略带紫色,紫中略带青色,宛如一朵朵盛开的莲花。盛一碗端上桌来,撒些葱末,白的白,绿的绿,嫩的嫩,煞是好看。
把自然界中不起眼甚至难以食用的物种发掘出来,找出食用之法,是许多“地方特色食物”的起源。就像没多少肉的蟛蜞,通过除余、捣碎、高温加热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分离出“有效成分”,再转化成易于食用的食物形态——像豆腐一样的“固体胶”,是江边人家的专利,也是蟛蜞最智慧的吃法。此吃法正应了庄子“无用之大用”之说。
蟛蜞豆腐,其独特的口感,惊艳舌尖,是爽口的“香”、软滑的“嫩”、原味的“鲜”,远胜于真正的豆腐。对此,吃货们有“形似豆腐花,鲜嫩赛河豚”之说。唐朝诗人白居易曾写有赞美蟛蜞的诗句——“乡味珍彭越,时鲜贵鹧鸪”。由诗句我们可推测,白居易虽吃过蟛蜞,却没吃过蟛蜞豆腐。他要是吃了蟛蜞豆腐,写出的诗句一定会更美妙,岂是“珍彭越”“贵鹧鸪”能比拟的?
天下既然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然也有“第一个吃蟛蜞的人”。因蟛蜞体形与螃蟹极为相似,古人曾将其误作螃蟹食用。《晋书·蔡谟传》云:“谟初渡江,见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原来,蟛蜞与螃蟹的滋味是不尽相同的。个中缘由,除蟛蜞比螃蟹肉少外,螃蟹食荤,蟛蜞食素,尤其是夏天的蟛蜞,以嫩苇叶为食,食之,鲜中稍带一股苦涩的草腥味。然而,冬天的蟛蜞则不同,它们躲在洞中冬眠,腹中空空。若此时捕而食之,必无草腥味,滋味最好。
曾经有一段时间,因长江开发过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江滩芦苇丛变少了,导致蟛蜞一度难觅踪影,让蟛蜞豆腐这道美味因稀而贵,身价倍增。近几年长江“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芦苇在江滩疯长,郁郁葱葱,密密麻麻,一片一片,一望无际。如此,芦苇丛中的蟛蜞,必定是子孙满堂,芸芸众众,如过江之鲫。倘若允许涉足江滩芦苇丛,你见到的该是怎样一幅生态、美丽、壮观的景象!
时代在变化,食物更丰富,美味何其多。虽说卑微的蟛蜞豆腐,并不在山珍海味之列,但何尝不是一道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这一款独特的江南美食,饱含了抹不去的记忆和乡愁,于我而言,是食谱上的头名“西施”、头名“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