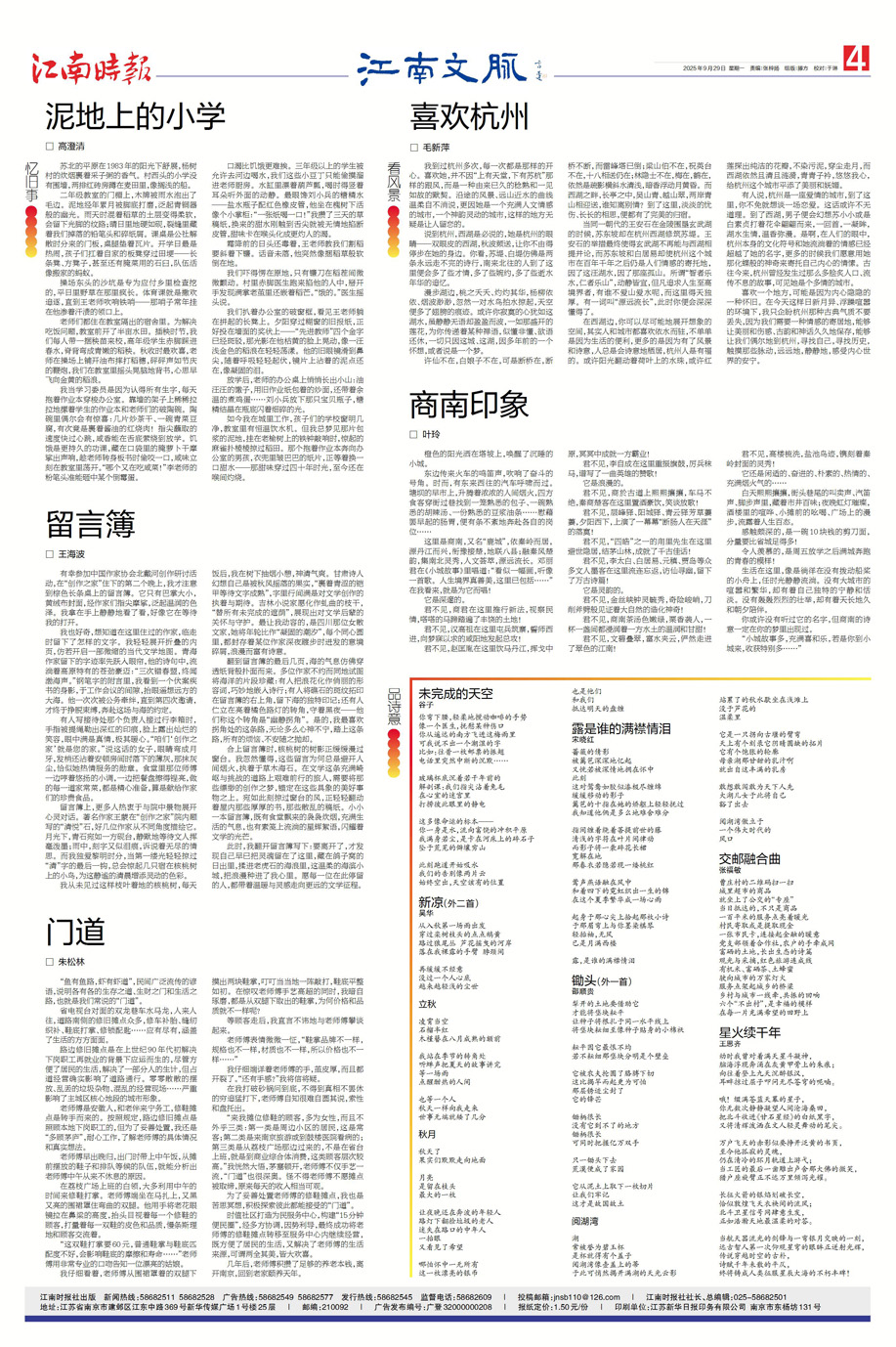泥地上的小学
□ 高澄清
苏北的平原在1983年的阳光下舒展,杨树村的炊烟裹着采子粥的香气。村西头的小学没有围墙,两排红砖房蹲在麦田里,像搁浅的船。
二年级教室的门楣上,木牌被雨水泡出了毛边。泥地经年累月被脚底打磨,泛起青铜器般的幽光。雨天时混着稻草的土层变得柔软,会留下光脚的纹路;晴日里地硬如砚,裂缝里藏着我们掉落的铅笔头和碎纸屑。课桌是公社解散时分来的门板,桌腿垫着瓦片。开学日最是热闹,孩子们扛着自家的板凳穿过田埂——长条凳、方凳子,甚至还有腌菜用的石臼,队伍活像搬家的蚂蚁。
操场东头的沙坑是专为应付乡里检查挖的,平日里野草在那里疯长。体育课就是撒欢追逐,直到王老师吹响铁哨——那哨子常年挂在他渗着汗渍的领口上。
老师们都住在教室隔出的宿舍里。为解决吃饭问题,教室前开了半亩水田。插秧时节,我们每人带一捆秧苗来校,高年级学生赤脚踩进春水,脊背弯成青嫩的稻秧。秋收时最欢喜,老师在操场上铺开油布摔打稻穗,砰砰声如节庆的鞭炮,我们在教室里摇头晃脑地背书,心思早飞向金黄的稻浪。
我当学习委员是因为认得所有生字,每天抱着作业本穿梭办公室。靠墙的架子上稀稀拉拉地摞着学生的作业本和老师们的破陶碗。陶碗里偶尔会有惊喜:几片炒茶干、一碗青菜豆腐,有次竟是裹着酱油的红烧肉!指尖蘸取的速度快过心跳,咸香能在舌底萦绕到放学。饥饿是更持久的功课,藏在口袋里的腌萝卜干摩挲出声响,趁老师转身板书时偷咬一口,咸味立刻在教室里荡开。“哪个又在吃咸菜!”李老师的粉笔头准能砸中某个倒霉蛋。
口渴比饥饿更难挨。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被允许去河边喝水,我们这些小豆丁只能偷摸溜进老师厨房。水缸里漂着葫芦瓢,喝时得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最眼馋刘小兵的糖精水——盐水瓶子配红色橡皮管,他坐在槐树下活像个小掌柜:“一张纸喝一口!”我攒了三天的草稿纸,换来的甜水刚触到舌尖就被无情地掐断皮管,甜味卡在喉头化成更灼人的渴。
霜降前的日头还毒着,王老师教我们割稻要斜着下镰。话音未落,他突然像捆稻草般软倒在地。
我们吓得愣在原地,只有镰刀在稻茬间微微颤动。村里赤脚医生跑来掐他的人中,掰开手发现满掌老茧里还嵌着稻芒。“饿的。”医生摇头说。
我们扒着办公室的破窗框,看见王老师躺在拼起的长凳上。夕阳穿过糊窗的旧报纸,正好投在墙面的奖状上——“先进教师”四个金字已经斑驳,那光影在他枯黄的脸上晃动,像一汪浅金色的稻浪在轻轻荡漾。他的旧眼镜滑到鼻尖,随着呼吸轻轻起伏,镜片上沾着的泥点还在,像凝固的泪。
放学后,老师的办公桌上悄悄长出小山:油汪汪的馓子,用旧作业纸包着的炒面,还带着余温的煮鸡蛋……刘小兵放下那只宝贝瓶子,糖精结晶在瓶底闪着细碎的光。
如今我在城里工作,孩子们的学校窗明几净,教室里有恒温饮水机。但我总梦见那片包浆的泥地,挂在老榆树上的铁钟敲响时,惊起的麻雀扑棱棱掠过稻田。那个抱着作业本奔向办公室的男孩,衣兜里皱巴巴的纸片,正等着换一口甜水——那甜味穿过四十年时光,至今还在喉间灼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