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诗潮汹涌至今,犹如一条奔涌的河流,既裹挟着泥沙,也沉淀着真金。在恒河沙数的诗歌写作者中,张国凡以其沉潜的姿态、坚韧的笔触,在时代的画布上勾勒出独特的精神轨迹。他的诗歌如同从火中淬炼的青铜,既保留着历史的厚重包浆,又闪烁着当代的锋芒光泽。当许多诗人在语言的迷宫中追逐炫技,或在私人化的情绪中沉溺时,张国凡始终坚守着诗歌的双重使命:以独特的表现形式承载时代的重量,以拓展的审美内容照亮精神的疆域。一位诗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不借助他人达成自己,如其能有一首诗能够赢得读者喜爱,甚至有那么一句能够传扬,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张国凡的诗歌往往书写前人所未有,《枪刺的正告》《雨花之歌》构成了南京城市诗歌的底色;“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更是成了打捞历史记忆的标志性诗句,为全国各地诗人拈手借用化用。张国凡的诗歌实践,正是这种艺术自觉的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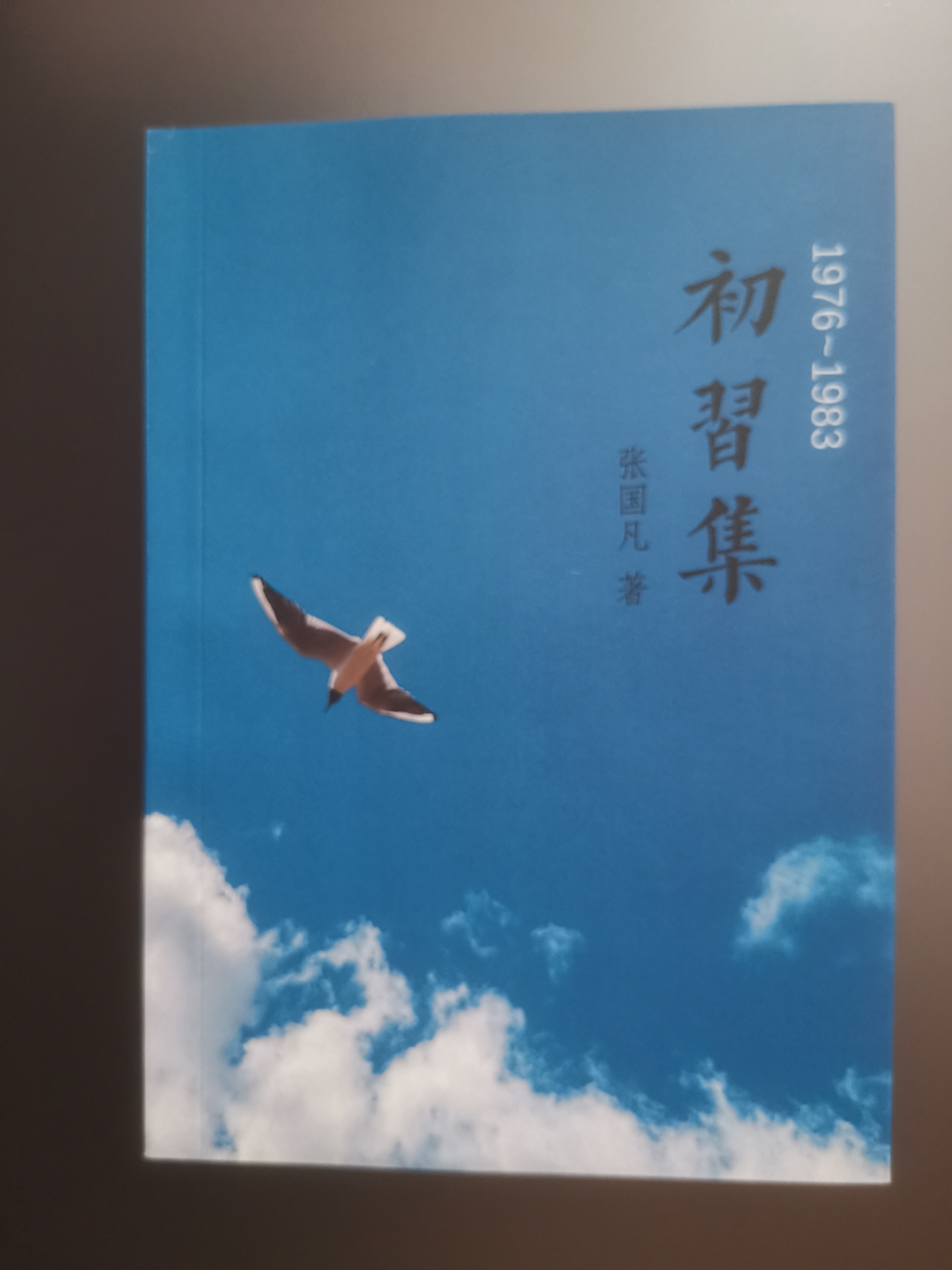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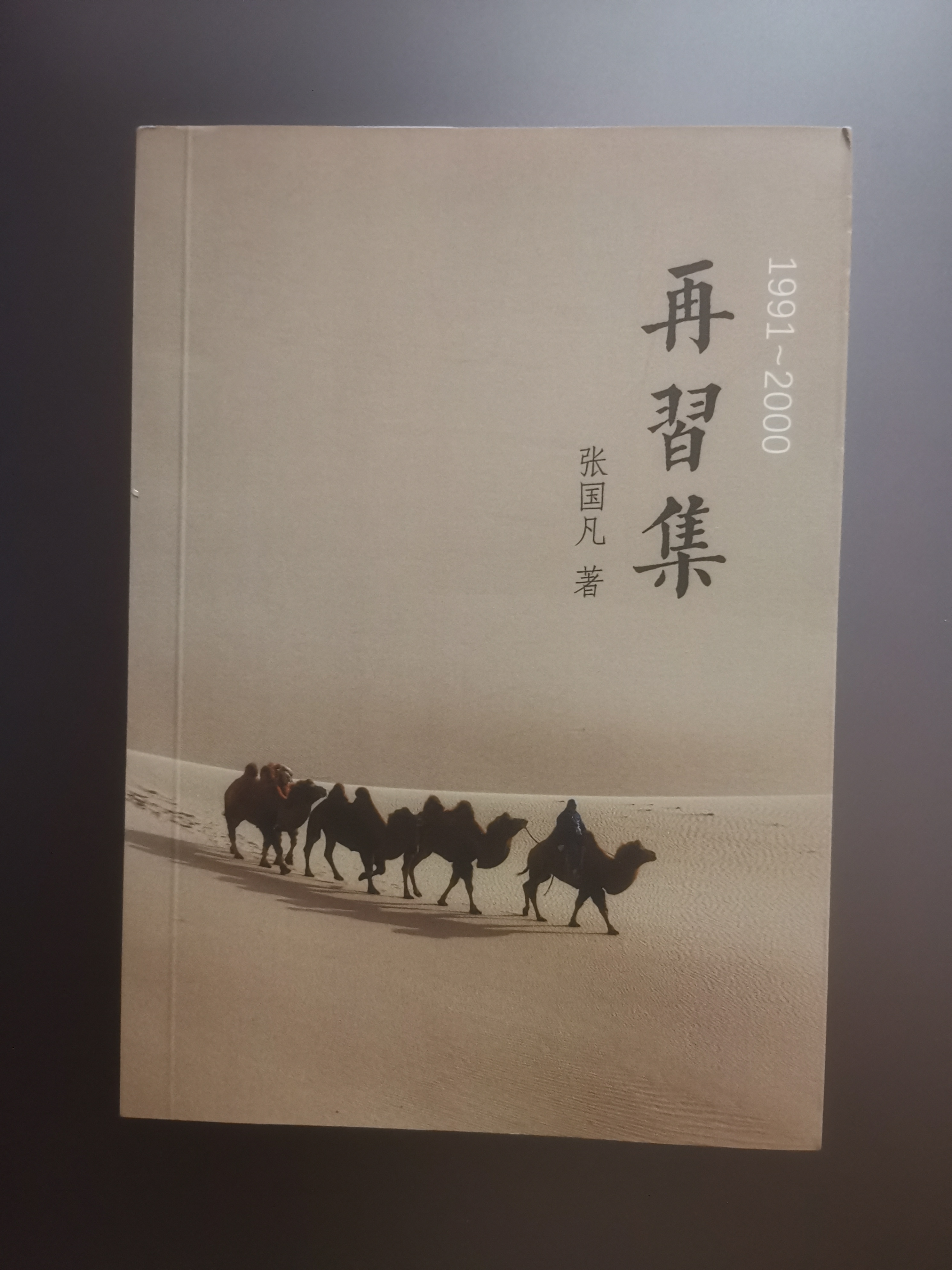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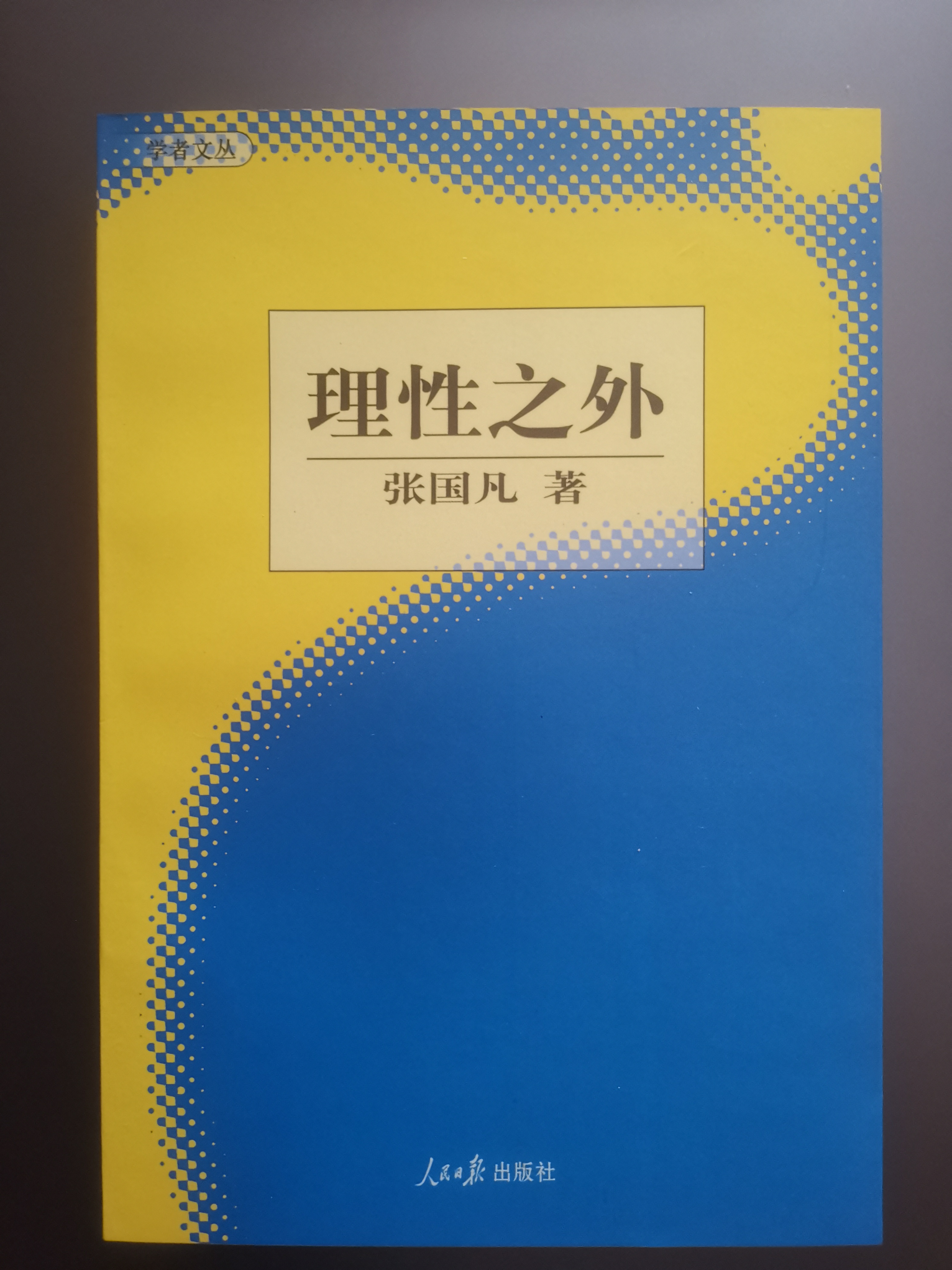
在张国凡《初习集》《再习集》《理性之外》诗歌选集之后,有理由期待即将出版的《攀登集》也会馈赠给读者非同寻常的文学享受。张国凡的诗歌阵列中,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记载,而是可以触摸的体温、可以倾听的脉动。他善于将宏大的历史叙事拆解为具象的诗性元素,让那些沉睡的过往在意象的碰撞中苏醒。《小雨:雨花台烈士陵园》中,“血纹和血纹手挽着手/唱亮火焰的春天”,这种将抽象精神具象化的笔法,打破了传统咏史诗歌的窠臼。雨水的“宁静”与碑文的“洁白”形成视觉对冲,而最终“站起一根顶天立地的骨头”,则完成了从自然景象到精神图腾的升华。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象征叠加,而是通过“淋湿初绽的诗句”这样的细节,将诗人的在场感嵌入历史语境,形成双向的精神对话。《八女投江》更彰显出诗人处理历史题材的独特匠心。“中国的江水/轻轻覆盖女儿的头顶/历史开始下雪”,开篇即以“雪”的意象覆盖了血腥的暴力,这种美学转化不是对历史的消解,而是以更具穿透力的诗性语言抵达本质。“民间的花轿在静美中等待”与“自己的江水却哭出大片大片的民族悲哀”形成残酷的对照,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创伤紧密缝合。诗人没有停留在悲情的宣泄,而是让“八个女儿,蔚蓝的目光/穿透岁月”,成为照彻未来的精神光源。结尾“中国的思念/永远夹杂着白发”,将历史的宏大叙事最终落定于个体的生命体验,这种"大历史"与“小叙事”的交织,正是张国凡历史题材诗歌的鲜明特征。《铜唢呐的铜》则展现了诗人对器物美学的深刻洞察。“从火中走出的一支队伍/进入黄色的沉默”,开篇即将铜唢呐的物理属性与精神属性并置。“为了旋律的光芒/希望挣脱着黑暗/把苦难托起”,这种将乐器视为历史参与者的视角,赋予了日常器物以史诗性的品格。诗人“再一次深入铜”的过程,实则是对民族精神内核的钻探——铜的坚韧、火焰的淬炼、旋律的飞扬,构成了民族性格的三重维度。这种从物质到精神的递进式书写,体现了张国凡对“文化是被构建出来的”这一命题的诗性回应。 在历史题材的处理上,张国凡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泛,又拒绝了私人化解读的狭隘。他如同一位考古者,在历史的地层中发掘出那些依然温热的精神碎片,再以诗歌的熔炉将其重铸为新的图腾。这种转化不是对历史的消费,而是让历史成为照亮当下的精神火炬,正如《枪刺的正告》中“历史的教训应当铭记:玩火者必将/自焚其身”,呼喊出对日本军国主义泛起的警示,诗句铿锵,始终保持着诗歌的现实在场感。
作为一位敏锐的城市观察者,张国凡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文本。他笔下的城市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丛林,而是充满生命呼吸的有机体,在拆迁与重建的阵痛中诉说着文化的嬗变。《推土机》以拟人化的手法,将机械的轰鸣转化为历史的低语:“推起陈旧。推起土/新鲜的土裸露出来/还有石子。石子自由的无产者/从此确立起来”。诗人没有简单地批判现代化对传统的碾压,而是在“推起时间/使黑暗一寸寸地转换为光明”的辩证中,捕捉着变革时代的复杂面相。 《五条巷》堪称城市变迁的史诗性书写。“成片的老房子瞬间拆除”带来的失落,与“安置楼不分伯仲/彼此抱怨地拥挤一团”的荒诞,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精神困境。诗人以近乎白描的手法罗列消失的物象:“老槐树、牵牛花的篱笆墙、老梧桐、水井、麻雀、瘸腿的老狗、垃圾车的枣红马”,这些碎片式的记忆拼贴,形成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集体缅怀。但诗歌的深度在于并非停留在怀旧的感伤,而是在“历史文化霞光”的重新照亮中,发现“生活的连绵”“情感的互动”“岁月的温馨”。从“灰色的大裤衩”到“石头卤菜店的半只烤鸭”,从“奥地利原公使馆”的发现到“高建中民间艺术收藏展”的即将开幕,诗人捕捉到了文化重建过程中的希望微光。《这条街》则聚焦于城市更新中的历史延续性。“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纵向历史的诗意表达,将物理空间提升至文化符号的高度。“新绿和乳白在这条街上纠缠”的意象,暗示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诗人在“旧式楼梯的拐角/碰到别人的爱情”的细节中,揭示出城市记忆的隐秘传承——那些看不见的情感脉络,往往比看得见的建筑更能维系文化的根脉。这种对城市肌理的诗意解构,超越了简单的空间叙事,进入了文化身份认同的深层思考。张国凡的城市诗歌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于他既不是传统的守旧者,也不是现代的拜物教信徒。他如同一位冷静的解剖者,在城市的血管中倾听文化的脉搏;又如同一位温情的缝合者,将断裂的记忆重新编织进当代生活。他的书写印证了“文化是被构建出来的”这一判断,在拆迁与重建的辩证中,诗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真正的城市文明,不在于建筑的高度,而在于记忆的深度。
张国凡的诗歌疆域不仅限于城市,更延伸至广阔的自然天地。他笔下的山川河流、草木鸟兽,都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承载着人文精神的符号载体,形成了自然与人文的互文性书写。《江南》以极简的笔触勾勒出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抓起一把泥土,轻轻一捏/流出碧绿的细雨”,开篇即将地理特征转化为诗性语言。“出淤泥而不染/是江南的灵魂”的断言,在“鱼篓”“桃花”等意象的映衬下,完成了从自然景观到文化品格的升华。诗人没有停留于江南的柔美表象,而是深入到地域文化的精神肌理,让自然景物成为人文精神的外在显现。《青海湾》则展现了诗人处理宏大地理意象的能力。作为李白《关山月》诗意当代延伸,诗歌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展开西部的精神图谱。“夜光杯中的葡萄”“明月腹地的机场”“高速路上的车灯”等意象,将古代边塞诗的苍凉与当代西部开发的豪情并置,形成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在杜鹃花的声音里/倾听芬芳,感受水石相遇的难弃”,这种通感手法的运用,打破了自然与人文的界限,让地理空间成为情感体验的延伸。诗人在“一百万只羊的温暖包围着耸立的/古寺”的意象中,找到了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生活的平衡点。《长城》一诗则将建筑奇迹转化为精神图腾。“每一块砖都咬着历史和风沙”的拟人化表达,赋予了物质存在以历史重量。“你的内心与力量,紧紧地与这片土地/连为一体”的断言,揭示出长城作为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核。诗人没有停留在对历史厚重感的渲染,而是在“血红、血红的中华之梦”中,让古老的长城获得当代的精神呼吸——这种呼吸,既来自历史的深处,也通向未来的远方。《雪豹》《神鸟》《立起的马》《英雄树》等诗作,则通过动物植物的意象,构建起独特的精神图腾体系。“雪豹的斑点都不一样/就像人类每一个人的指纹”,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呼应了艺术家"不借助他人达成自己"的追求;“神鸟把预言刻在心灵,也把祝福洒向阳光”,赋予了自然生灵以精神指引的功能;“立起的马”的“不屈的头颅”和“钢铁构架”,成为意志力量的象征;“英雄树”的“站着生也站着死”,则彰显了精神品格的崇高性。这些自然意象的符号化处理,使张国凡的诗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图腾体系,既扎根于大地,又翱翔于天空。在自然与人文的互文书写中,张国凡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跨越。他的每一首山水诗,都是文化基因的解码;每一次自然咏叹,都是精神家园的回望。这种书写方式,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文化底蕴,又融入了现代的生态意识和人文关怀,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诗歌美学。
张国凡的诗歌始终保持着鲜明的精神向度,这种向度既扎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又升华至民族的精神高度,形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情感升华路径。《只要你说一声:祖国》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将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实际上,只要你说一声/说一声:祖国/我的双眼就会蒙上一层泪水”。这种抒情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建立在“曾经是一个兵”的生命体验之上,建立在“走遍祖国一半的土地”的亲身经历之上。“我的每一块骨头/都咬着火焰”的断言,将抽象的爱国情怀转化为可感的生命体验,具有强大的情感冲击力。《我说:党》则展现了诗人对政治抒情诗的现代性探索。诗歌没有陷入概念化的图解,而是从“大雪纷飞的中午抵达遵义”的个人记忆切入,在“赤水河的透明冰块”“娄山关松树的墨绿”等具体意象中,完成对历史的诗意重构。“这个中国的声音,这个人民的声音/这个个人的内心的声音”的三重强调,将宏大叙事落实到个体体验,避免了政治抒情诗常见的空泛。诗人将历史的“转折”与个人的“激情”相勾连,在“霜天红叶”“长安大街灯火”的意象中,让政治情感获得了美学的支撑。《英雄树》通过对一棵枯树的礼赞,构建起精神品格的象征。“站着生也站着死”的生命姿态,成为英雄主义的生动写照。“弯曲着干枝/将狂风撕成纸一样的碎片”的意象,将抽象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具体的视觉画面。诗人在“不知道是什么夺去了你的生命”的设问中,引发对英雄遭遇的深沉思考,而“你还是选择了属于你的姿势——/与地平线保持着垂直”的结尾,则将这种思考升华为对精神独立性的坚守。《安宁或者乡间》则回归到个体生命的精神家园。“天的尽头是炊烟,白云/在远远的高处/离我最近的是一棵大树”的意象,构建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图景。诗人在“兄弟的面容和黄昏/摇成路边的草药”的转化中,让亲情获得了治愈的力量。“在无边无际的善良中行走”的结尾,既是对乡间生活的礼赞,也是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在苦难与安宁的辩证中,显现出生命的韧性。 张国凡的抒情诗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在于他始终保持着情感的真实性和体验的独特性。他既不回避宏大的精神主题,又能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生命体验;既继承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又融入了现代的思考维度。这种从个体情感到民族精神的升华,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有机的融合,正如他在诗中所言:“从一棵绿草起飞/大雪飘落,树根拖动/全部的历史”,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民族的历史记忆在诗歌中获得了完美的统一。

张国凡
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碎片化的当下,张国凡的诗歌实践如同一股清流,提醒我们诗歌应有的重量和温度。他的诗歌如同从火中淬炼的青铜,既保留着历史的包浆,又闪烁着时代的锋芒;既继承了传统的基因,又融入了现代的血液。从历史题材的诗性转化,到城市肌理的诗意解构,从自然人文的互文书写,到精神向度的抒情建构,张国凡始终坚守着诗歌的双重使命: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拓展的审美内容。 他的创作在吸收昌耀、叶赛宁、里尔克等中外诗人营养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独立的艺术品格,在纷繁的艺术潮流中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向度。他的诗歌是“被构建出来的”文化的生动例证,那些看似与传统不一致的表达,实则是个人艺术成熟的标志,达到了“见情见性的深度”。当许多诗歌在速朽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时,张国凡的诗歌以其青铜般的质地,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对“带翅膀的图腾”这一诗歌本质的生动诠释——既有飞翔的灵性,又有扎根的厚重;既有象征的意味,又有实在的质感。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诗歌必将继续闪耀其独特的光芒,为时代留下深刻的精神印记。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名誉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