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位文化大家,一百段情爱故事,在一本长达498页的沉甸甸著作中,以风雨相随、情深意远的言说方式,再现跌宕人生中的离愁别绪、曲折浪漫亦或相濡以沫,让来自历史记忆的图像和声音,穿过时光迷雾,蒙太奇般彰显耐人寻味的审美影踪和光亮——老友徐廷华最新出版的纪实散文集《百年百人情与事》大化文史、取样情意,笔走100年,为我们捧出了一桌中国文化大咖们快意“江湖”、爱恨交融的情感美学大餐。
用“百年彩虹鉴风雨,百朵玫瑰透心香”来形容这桌大餐的感情吸引力、时光穿透力以及文本震撼力,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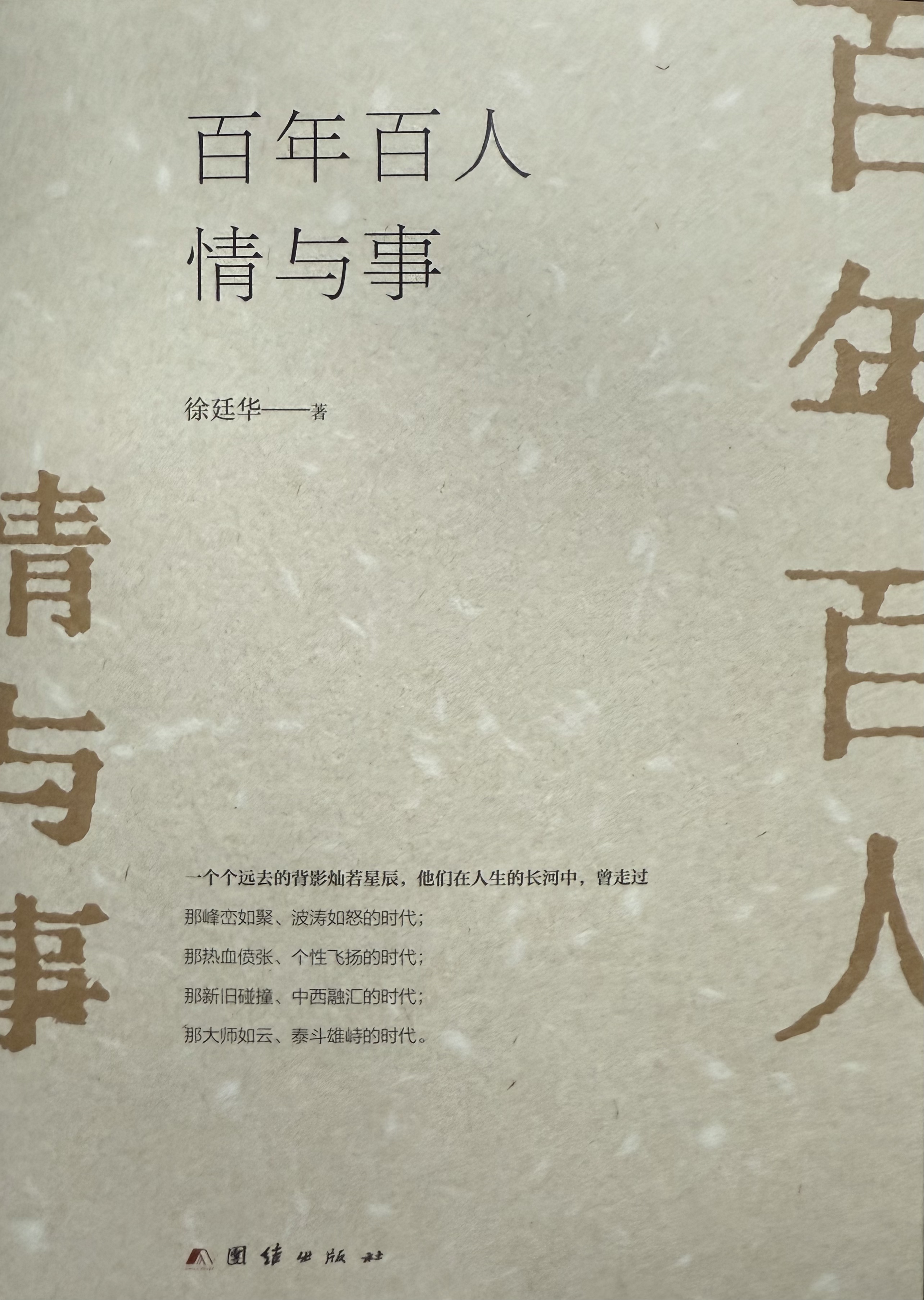
作为长期从事散文写作的高手,徐廷华的创作成果中,与近现代历史文化名人相关联的文史类散文作品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顶流报刊都曾留下过他的墨痕。眼前这部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百人情与事》,便是他以文学加史学的眼光打量文海旧事,发现其中电光石火、飞花流萤的集中体现。全书按所写人物身份分为艺术大师、文坛大家、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四大版块,每一版块都通过详实的史料、动人的笔墨、曲折的故事刻画人物、感知爱情,使得大众所熟知的一个个历史名人更加有血有肉、有气有神地刷新固有影像,显现出原本就应该有的人间烟火气。
说到“情”,说到“爱”,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恐怕要数忠贞不渝的爱情了。徐廷华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序中坦言,在还原笔下人物情感故事时,他非常注重“写他们甘苦与共的夫妻之爱,记他们鸿雁传书的相恋之旅,述他们琴瑟和谐的美满生活”,基于这样的创作认知,我们看到了冼星海与钱韵玲这对从战火中走来的亲密伴侣;我们听到了周信芳与裘丽琳在人生舞台唱出的生死恋歌;我们还体会到了赵元任与杨步伟这对“神仙伴侣”的美好姻缘;感受到周巍峙与王昆用歌声唤来的意中人……这一对对忠贞于爱情、坚定守护着爱的纯度、烈度的有情人,和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用“爱”、用“情”维系着家庭美好的伉俪夫妻一样,把烦恼化为轻烟,将苦难藏在箱底,用云淡风轻破解风雨雷电,让我们透过人性的光亮收获由衷的感动。这里面,冼星海与钱韵玲是在前往延安的途中结为夫妻的,他们相互扶持、共度难关,后来,冼星海被派往苏联学习,期间不幸病故。作者在此写道“而这一切,远在千里外的钱韵玲一无所知,他仍然痴情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当冼星海逝世的噩耗传到延安,钱韵玲失声恸哭,她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恒。”平平淡淡的叙述中,蕴含着痛彻心扉的情感波澜,爱之深切,文字尽显。
由于所写人物绝大部分都处在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因而,他们的爱情故事有许多也不是无风无浪、一路爱到底的,面对错综复杂的情感考题,徐廷华总是深入追踪,他在赞颂忠贞爱情的同时,还满怀深情地“忆他们悲欢离合的凄美爱情,状他们缠绵缱绻的苦恋之旅,歌他们功高德望的事业成就”,全力透过岁月烟雨,发现他们曲折离奇爱恋故事中的情感和人性珍宝。
国画大师李苦禅曾经历过三段不寻常的婚姻,第一任妻子携手途中不幸中风身亡;第二任妻子原本以为能相伴到老,却背着他偷偷地红杏出墙;直到遇见第三任妻子后,画家的情感构图才落下温润、生动的墨色。两人恩爱相伴,即使在特殊年代大师落难之际,妻子也忠贞不改,在苦苦相盼中熬过了寒冬。记述此事的徐廷华满怀敬重之情,还原了苦禅大师的“苦禅”人生;与之相似的还有著名言情小说家张恨水。他在家人的安排下违心地接受了包办婚姻的相亲,可到现场后发现对方居然很入自己和家人的“眼”,便爽快同意了这门婚事。哪知婚礼将新娘迎娶进门后,“美娇娘”却变成了“丑猪婆”,原来相亲时是妹妹假冒了姐姐。错了只得默认,张恨水放下芥蒂、面对现实,孤独地等待着真正的爱情,最后终于找到自己心中的知己……徐廷华同样以生动、感人的文字记录下这位以写作《啼笑因缘》名世的情感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啼笑因缘”……像这种历经各种磨难,在分分合合中找到真爱,修成正果的爱情故事,在各领域文化名人、大家中并不少见,翻看这部著作,徐悲鸿、潘玉良、沈从文、戴望舒、陈寅恪、顾维钧等人多舛的命运都是这样让我们感慨,让我们看到了“情”的通透、“爱”的坚韧的。
当然,百年文化星空下,情与爱作为一颗颗大星发出的人性光亮,其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远不只这些。在徐廷华的著作中,一些带有较多浪漫、超然色彩的情爱故事,也以其刷新世俗认知的“逆光”冲击力,感动着被“习惯”圈定的阅读者。
在艺术追求、文化碰撞、情感渗透、生活体察的奇妙火花间,我们能看到齐白石、梁实秋等人经历的“柏拉图”式的“忘年恋”;在相思而又相敬、相知而又相远的透明图景中,我们能看到王洛宾与三毛、金岳霖与林徽因等人“心中有你常相思,月下无缘难牵手”,一生只与你情意互达的“精神恋”……这许许多多情与爱交融的往事,这许许多多乐与忧同在的历史镜头,仿佛幽谷鸟鸣,让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文事追索与阅读中,感受到由声音调制的情感色彩,它们是写实的,又是写意的;是生活的,又是文艺的,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
细细品味徐廷华推荐给我们的这些人物和故事,这些图像和场景,我觉得,该书有三大写作亮点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把文华当作调色板。
进入文史的天空,面对的,是一件对繁琐、枯燥的历史资料不断翻拣、掂量的苦活,徐廷华自己也说,写这类文章要“读万卷书”,要“在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书籍中,一点一点积累资料,东一点西一瓢,是随寒暑晨昏的时间流逝,集腋成裘,厚重了再爬疏打磨、理出人物脉络,分析提炼、斟酌取舍”。就是在这样的苦活、累活面前,这位老作家倾心尽力,成就了一篇篇有眉目、有分量、有温度的文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像这种文史类的稿件有不少人都在写,但他们大多受限于过去的事实,写出的作品史料虽充足,生动性却不够。而徐廷华则是“选取一个新颖的角度”“用自己所熟悉的散文笔调,倾注一腔热情于笔端”,因而,他所道出的人和事侧重以灼灼文华为调色板,在充分占有事实的基础上,显现出提神布彩、血色丰盈、进退有致的文本表情。
其二,用情感作为粘合剂。
文史中的事情基本都是以“发生”作为不二看点的,里面的人物情感有时是无法投射于事实本身的,因而写作者对材料的处理往往多罗列式的陈述。作为不甘被动写作的散文作家,徐廷华充分利用自己所独具的文学优势,以心度心,主动挖掘笔下人物内在的情感光亮,加上自身激发出的创作情感,使之成为事件延伸、融通的粘合剂,这样一来,作品便在起、承、转、合中有了更多的回旋空间,人物和事件的可读性、可信度也随之大大增强。
其三,将受众看作指路标。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名人效应便是抓住他们目光的不可抗引力,在了解完这些闪光人物的专业成就后,他们的情感生活自然成了更加诱人的“香料”;而随着文学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作家作品的市场“卖点”问题也日益现实地摆到了出版商面前。正是在这一“双向需求”背景下,徐廷华这部书稿的写作与出版部门的需求找到了契合点,这本书最终以非自费的形式出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以受众为指路标,在挑剔的阅读市场,有着不容忽视的接受潜力。
一百年风声雨声,一个个远去的背影,就像一首既优美又隽永的诗,长句短句间,旧的瓦檐花草渐次模糊,情爱的遗韵依然在烟云中游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