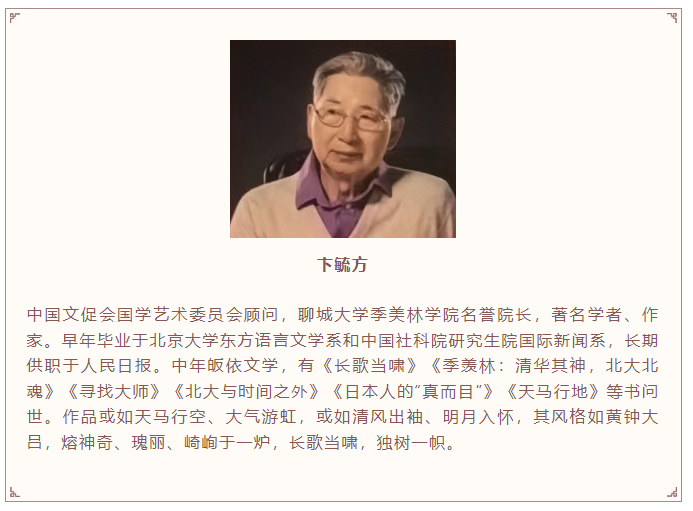初一的语文老师我已忘了姓名——按说老师记住每一个学生难,学生记住单一的老师易,我到底不算好学生——印象中是苏南人,黑而干瘦,他讲《诗经•伐檀》,用略带乡音的语调吟诵: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一诵起来,就别有味道,格外容易记忆。
课后,我向老师请教《诗经》中的另一首《斯干》,这是我的课外书,老版本,没有注释,首节是:“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老师轻轻诵了一遍,“斯干”,听他念的是“斯jiàn”,显然是“河之干兮”之“干”的异音字。接下去,老师说:“我要备课,查了字典,再告诉你。”
他说得十分自然,一点也没有端老师的架子。我顿时肃然生敬,觉得是遇到了坦率而又严谨的好老师。
初二的语文老师是刘祚久。我因病休学一年,属蹲班生。首篇作文,写课外劳动,我模仿郭沫若早期的散文笔调,写得声情并茂,古色古香。刘老师认为这绝不可能是我写的,连他也写不出来,肯定是抄袭,把我好生尅一顿。
次篇是民歌,我写成顺口溜。老师说:“这篇像你写的。”第三篇回到记叙文,老师说:“你进步很快。”第四篇,夹叙夹议,老师用红笔批了两个大字:“传观”,并让我在课堂上朗读。
恰值“三年困难时期”,我走读,中午散了学,照例应该回家吃饭,有一阵子,出了校门,我选择的却是相反的方向,沿小洋河朝东走,百米外有道闸,闸旁有个足以容身的大洞,是天然的土室,正南其户。想起金圣叹的文章:“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我独坐洞府,南面称王,抓紧吞咽精神食粮,也是不亦快哉!
那日子穷是穷,却穷得极有志气,套用孟子的话:“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帅气,气帅体,一顿两顿不吃,无碍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八十年代,射阳,后排从左至右,杨忠茂、汪祥喜、袁庆国)
一天,刘老师突然出现在洞前,我慌忙站起,刘老师打量洞穴,除了我坐地铺的一束干草,此外,什么也没有。老师拿过我手中的书,是《古文观止》,他翻了翻,啥也没讲,把书还我,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离去。
我复坐地,翻到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大声朗诵:“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眼前荡荡漾漾的小洋河水,顿时化作滚滚滔滔的长江。
初三的语文老师我也忘了姓名,从外地调来的,好像一年后又调走了。性格极为开朗,身板宽,嘴巴阔。或许不是这样,无奈我的记忆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宛如中国画的散点透视,远山无石,远树无枝。一次作文,写劳动课摘棉花,我参照《林海雪原》中东北民主联军清剿残匪的场面,好一番天花乱坠,落英缤纷,老师表扬说“绘形绘色”。又一次,写帮社员冒雨抢收庄稼,我把《西游记》中战天斗地的骈词化作时尚的口语,老师批示说“活学活用,推陈出新”。并非篇篇如此,但是,我的记忆我做主,它是一种既玄妙又自私的本能,它会筛选,淘汰平庸凡俗,强化积极向上——实不相瞒,少年人的虚荣,是早已渗透到骨子里的。

(1967年,南京玄武湖,后排从左至右,唐晋元、胡礼海、曹如璧)
初中毕业前,老师送我一本《红旗歌谣》,这是那个时代的强音,属于最深情最饱含期待的礼品。然而,想来是在翻天覆地的六十年代,我竟然没有能像保护圣物一样把它保存下来。本来是件值得传家的盛事,到头来却变成无尽的自责自怨。
写作此文前,我调动各种关系,包括老同学,以及母校的现任领导,请他们帮助回忆、查找那位老师的姓名,企图将功补过,赓续旧缘。毕竟相隔太久,圈子内的几位老同学已不复记忆,母校倒是提供了一份数百人的大名单,让我自己辨认。我恰如面对远景中的一抹人影,有道是远人无目,搞不清哪个名字后面隐藏着青睐过我的那双明眸。
我只有寄希望于大脑的神经回路,渴盼哪一天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我也祝愿随着生化科技发展,有朝一日能推出“记忆维生素”“记忆复康胶囊”,当然,能直接推出“记忆超市”更好,供有心人如我者购买某段特定时光的完整记忆。
高一的语文老师是丁瑛。曾经在初中教过我一段,算是老老师了。他是我的雕刻圣手,主要故事,我在《七拐八拐就拐向了北大》一文中说过,在此避开,另讲一件小事。
星期六晚上,我在电影院门口遇着丁老师。他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四顾无处存放,就让我找个地方保管。
我把车搁在两百米外的曹如璧家。
当日演的是《刘三姐》,未等结束,我起身离场,把车子推回来,在门外等丁老师。
丁老师看到我笨拙的推车姿势,惊讶地问:“你还不会骑车?”
“不会。”我老实回答。那时自行车属于高档用品,家里有两辆,分别为父亲、大哥拥有,平常不让我们碰。
“你书看得很多,生活阅历也比一般同学丰富(暑假我刚刚去过南京),但你缺乏生活技能,记住,凡你做过的事情,以及掌握的本领,将来都是你写作的宝贵材料。那天我瞧你在朝阳桥头帮别人推车(其实是帮一个同学的爷爷),那也是体验。”
老师说的对,生活是部大书,学问更是无时没有,无地不在。我至今七老八十,依然在学“吹鼓手”,不觉为时已晚,反而兴致勃勃,使自己的大脑神经元始终处于活跃状态,这都是为了“体验”。
高三的语文老师是纪锡生,顾名思义,乃江南无锡人氏。江南是文化的高地,纪先生又是出身文化世家,学问好,脾气好,一旦走近,是可以敞开肺腑讲暖心话的。详情大略,也已见《七拐八拐就拐向了北大》一文,这里,同样讲一件生活中的小事。
是高三上,星期天,我去街上饭店改善伙食,恰巧碰上了纪老师。老师招呼我一起坐,另外加了两道菜——如此殊遇,今人也许司空见惯,当日却是出格逾矩。
吃饭间,老师指着桌上的菜肴,借题发挥,说:“少年人的文章,要像西红柿炒鸡蛋,既好看,又好吃;中年人的文章,要像红烧昂刺鱼,虎头虎脑,韵味十足;老年人的文章,要像青菜豆腐汤,一清二白。”
这是把只可意会的人运与文运的纠缠纠葛,归真反璞,形象化为通而俗之的言传,既可口可心,又醒神醒脑。
本世纪初,我去盐城,邀在盐的老同学聚会,也请了纪老师夫妇(时任教盐城师专)。吃饭时,我特意点了上述三道菜。老师记性好,席上,他搛起一块豆腐,冲着我,幽幽地说:“你现在的文章,就像红烧昂刺鱼。我现在的讲课,就是青菜豆腐汤了。”
我说:“哪里,我还停留在西红柿炒鸡蛋。”
众人讶异,我也不予说明,故意打哈哈,搪塞说:“老师知道,这是我的保底菜,几十年走南闯北,一直改不了老胃口。”

(最佳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