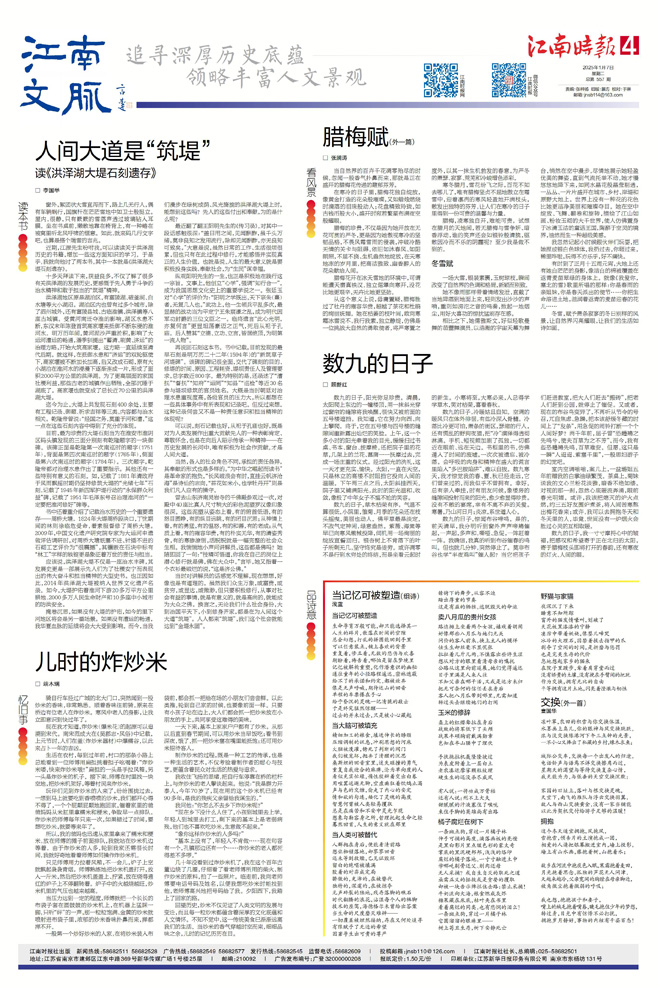人间大道是“筑堤”
读《洪泽湖大堤石刻遗存》
□ 李国举
窗外,絮团状大雪直泻而下,路上几无行人,偶有车辆蜗行,国旗杆在茫茫雪地中如卫士般挺立。屋内,很静,只有簌簌的雪落声透过玻璃钻入耳膜。坐在书桌前,懒散地靠在椅背上,有一种蜷在被窝里听北风呼啸的惬意。如此,就来码几行文字吧,也算是搭个瑞雪的吉兆。
近期,江源先生吩咐我,可以读读关于洪泽湖历史的书籍,增加一些这方面知识的学习。于是乎,我就向他讨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洪泽湖大堤石刻遗存》。
十多天拜读下来,获益良多,不仅了解了很多有关洪泽湖的发展历史,更感慨于先人勇于斗争的治水精神和敢于担当的“筑堤”精神。
洪泽湖地区原是湖泊区,有富陵湖、破釜涧、白水塘等大小湖沼。湖泊区内也曾有过多个城市,除了泗州城外,还有富陵县城、古临淮镇、洪泽镇等八座古城镇。受黄河南迁夺淮的影响,湖区水患不断,东汉末年陈登首筑高家堰来抵御不断东侵的淮河水。明万历年间,黄河泥沙严重淤积,影响了大运河漕运的畅通,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济运”的治理方略,开始大筑高家堰。这方略一直延续至清代后期。就这样,在抵御水患和“济运”的双轮驱使下,高家堰被不断加长加高,后又改成石砌,原有大小湖泊在淮河水的浸漫下逐渐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2000平方公里的洪泽湖。为了更高层面的家国社稷利益,那些古老的城镇作出牺牲,全部沉睡于湖底了。高家堰也就变成了总长近70公里的洪泽湖大堤。
迄今为止,大堤上共发现石刻400余处,主要有工程记录、御题、祈求吉祥等三类,内容都与治水相关。乾隆帝曾说:“经国之务,莫重于河和漕。”这一点在这些石刻内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目前,最为珍贵的大堤石刻当为在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发现的三面分别刻有乾隆题字的一块御碑。该碑正面是乾隆第一次南巡时的题字(1751年),背面是第四次南巡时的题字(1765年),侧面是第六次南巡时的题字(1784年)。三次题字,乾隆帝都对治理水患作出了重要指示。其他还有一些特别有意义的石刻。如,记载了1881年清政府于风雨飘摇时期仍坚持修筑大堤的“光绪七年”石刻,记载了1945年新四军护堤行动的“永保群众利益”碑,记载了1951年毛泽东号召治理淮河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碑等。
书中还着重介绍了记载治水历史的一个重要遗存——周桥大塘。1824年大堤周桥段决口,丁忧期间的林则徐临危受命,着素服督修了周桥大塘。2009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家为大运河申遗做评估调研时,对周桥大塘纸塞不进、针插不进的石砌工艺评价为“很震撼”,其镶嵌在石块中标有“林工”字样的铁锭更是象征着万世的责任与担当。
应该说,洪泽湖大堤不仅是一座治水丰碑,其发展史更是一部展示先人们为了社稷安宁而表现出的伟大奋斗和担当精神的大型史书。也正因如此,2014年洪泽湖大堤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大堤护佑着淮河下游20多万平方公里耕地、2000多万人民生命财产和10多座中小城市的防洪安全。
掩卷沉思,如果没有大堤的护佑,如今的里下河地区将会是另一番场景。如果没有漕运的畅通,我华夏血脉的延续将会大大受到影响。而今,当我们漫步在绿树成荫、风光旖旎的洪泽湖大堤上时,能想到这些吗?先人的这些付出和奉献,为的是什么呢?
最近翻了翻王阳明先生的《传习录》,对其中一段话感触很深:“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大意是说,虽然日常的工作、生活很烦很累,但也只有在此过程中修行,才能感悟并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也就是说,人生的最大意义就是要积极投身实践、奉献社会,为“生民”谋幸福。
纵观阳明先生的一生,也正是积极地在践行这一宗旨。文事上,他创立“心学”,强调“知行合一”,成为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之一。张廷玉对“心学”的评价为:“阳明之学既出,天下宗朱(熹)者,无复几人也。”武功上,他一生领兵平乱多次,最显赫的战功当为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更显坦荡豪迈之正气,死后从祀于孔庙。后人赞其“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再说回石刻这本书。书中记载,目前发现的最早石刻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新筑草子河堤碑”。该碑的碑记很全面,交代了碑刻的目的、修堤的时间、原因、工程耗资、堤坝责任人及管理要求,总字数近800字。最为特别的是,还录述了“漕抚”“督抚”“知府”“运同”“知县”“巡检”等近30名参与堤坝修筑的官员姓名。大概是当时朝廷对治理水患重视度高,各级官员的压力大,所以都想在一些具体事务中有所表现和记录吧。但反过来想,这种记录何尝又不是一种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的体现呢?
可以说,刻石记载也好,从祀于孔庙也好,既是对为人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先人的一种表彰肯定、尊敬怀念,也是在向后人昭示传承一种精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唯有积极为社会作贡献,才是人间大道。
当然,各人的社会角色不同,承担的责任各异,其奉献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革命家的抱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诗仙的志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则是我们凡人应有的操守。
曾去山东济南灵岩寺的千佛殿参观过一次,对殿中40座比真人尺寸稍大的彩色泥塑罗汉像印象很深。这些泥塑从姿态上看,有的俯首低语,有的怒目圆睁,有的纵目远眺,有的闭目沉思;从神情上看,有的勇猛,有的愠怒,有的和善,有的老成;从气质上看,有的雍容华贵,有的朴实无华,有的清姿秀骨,有的寒碜潦倒,活脱脱就是一幅完整的社会众生相。我惴惴地小声问讲解员,这些都是佛吗?她随即回了一句:“技精可悟道,你我在自己的岗位上潜心修行就是佛,佛在大众中。”言毕,她又指着一个衣衫最破烂的说,“这是济公佛。”
当时对讲解员的话感觉不理解,现在想想,好像也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众生万象,或富贵,或贫穷,或显达,或微渺,但只要积极修行,从事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是有意义的,就是高尚的,就能成为大众之佛。换言之,无论我们什么社会身份,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齐家,都是在为人间这个大道“筑堤”。人人都来“筑堤”,我们这个社会就能达到“金堤永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