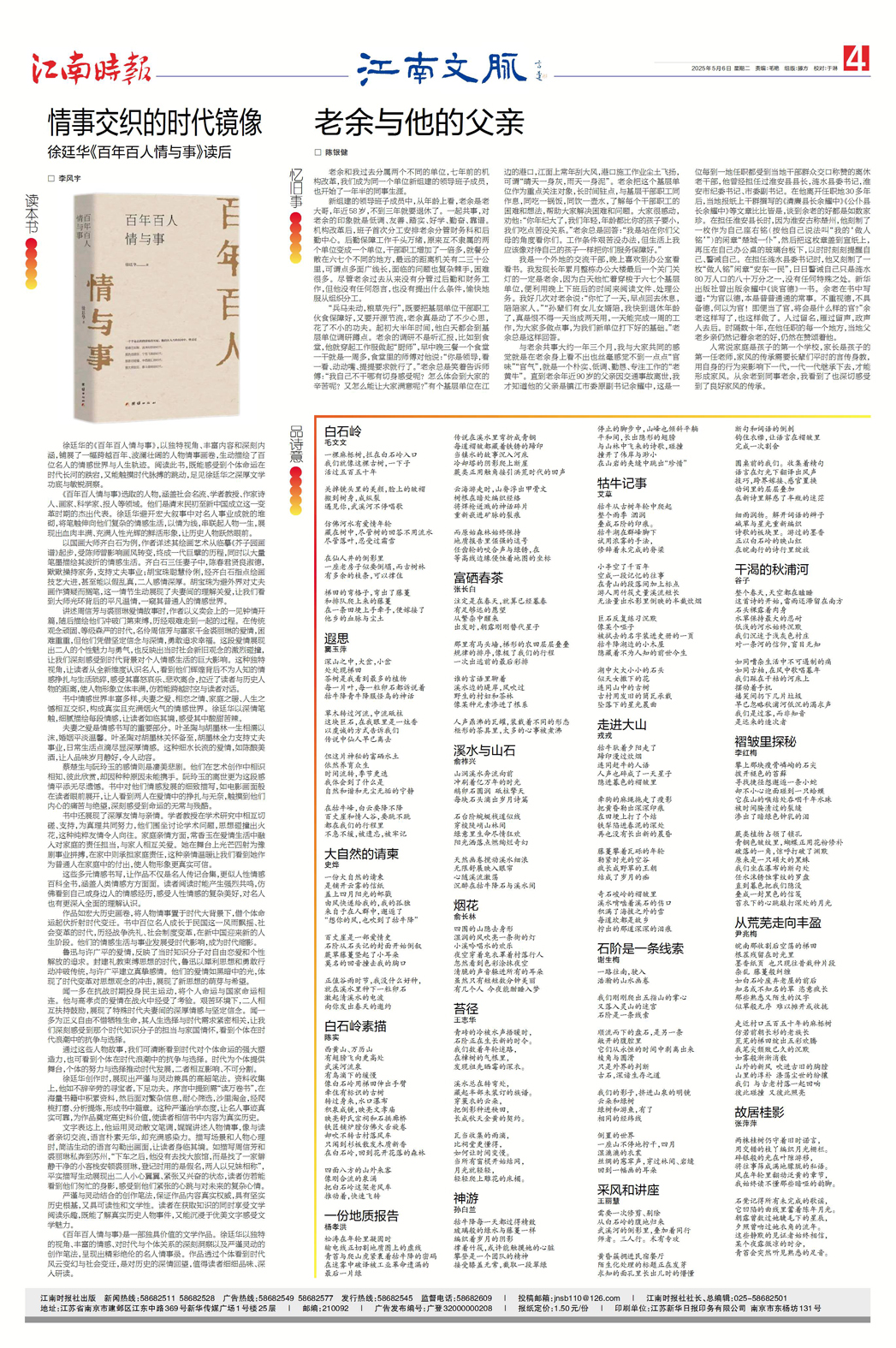老余与他的父亲
□ 陈银健
老余和我过去分属两个不同的单位,七年前的机构改革,我们成为同一个单位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成员,也开始了一年半的同事生涯。
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成员中,从年龄上看,老余是老大哥,年近58岁,不到三年就要退休了。一起共事,对老余的印象就是低调、友善、踏实、好学、勤奋、靠谱。机构改革后,班子首次分工安排老余分管财务科和后勤中心。后勤保障工作千头万绪,原来互不隶属的两个单位变成一个单位,干部职工增加了一倍多,就餐分散在六七个不同的地方,最远的距离机关有二三十公里,可谓点多面广线长,面临的问题也复杂棘手,困难很多。尽管老余过去从来没有分管过后勤和财务工作,但他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提出什么条件,愉快地服从组织分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既要把基层单位干部职工伙食保障好,又要开源节流,老余真是动了不少心思,花了不小的功夫。起初大半年时间,他白天都会到基层单位调研蹲点。老余的调研不是听汇报,比如到食堂,他就穿起工作服做起“厨师”,早中晚三餐一个食堂一干就是一周多,食堂里的师傅对他说:“你是领导,看一看、动动嘴、提提要求就行了。”老余总是笑着告诉师傅:“我自己不干哪有切身感受呢?怎么体会到大家的辛苦呢?又怎么能让大家满意呢?”有个基层单位在江边的港口,江面上常年刮大风,港口施工作业尘土飞扬,可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老余把这个基层单位作为重点关注对象,长时间驻点,与基层干部职工同作息,同吃一锅饭,同饮一壶水,了解每个干部职工的困难和想法,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和问题。大家很感动,劝他:“你年纪大了,我们年轻,年龄都比你的孩子要小,我们吃点苦没关系。”老余总是回答:“我是站在你们父母的角度看你们。工作条件艰苦没办法,但生活上我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把你们服务保障好。”
我是一个外地的交流干部,晚上喜欢到办公室看看书。我发现长年累月整栋办公大楼最后一个关门关灯的一定是老余,因为白天他忙着穿梭于六七个基层单位,便利用晚上下班后的时间来阅读文件、处理公务。我好几次对老余说:“你忙了一天,早点回去休息,陪陪家人。”“孙辈们有女儿女婿陪,我快到退休年龄了,真是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用,一天能完成一周的工作,为大家多做点事,为我们新单位打下好的基础。”老余总是这样回答。
与老余共事大约一年三个月,我与大家共同的感觉就是在老余身上看不出也丝毫感觉不到一点点“官味”“官气”,就是一个朴实、低调、勤恳、专注工作的“老黄牛”。直到老余年近90岁的父亲因交通事故离世,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镇江市委原副书记余耀中,这是一位每到一地任职都受到当地干部群众交口称赞的离休老干部,他曾经担任过淮安县县长,涟水县委书记,淮安市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在他离开任职地30多年后,当地报纸上干群撰写的《清廉县长余耀中》《公仆县长余耀中》等文章比比皆是,谈到余老的好都是如数家珍。在担任淮安县长时,因为淮安古称楚州,他刻制了一枚作为自己座右铭(按他自己说法叫“我的‘做人铭’”)的闲章“楚城一仆”,然后把这枚章盖到宣纸上,再压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警诫自己。在担任涟水县委书记时,他又刻制了一枚“做人铭”闲章“安东一民”,日日警诫自己只是涟水80万人口的八十万分之一,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新华出版社曾出版余耀中《谈官德》一书。余老在书中写道:“为官以德,本是普普通通的常事。不重视德,不具备德,何以为官!即便当了官,将会是什么样的官?”余老这样写了,也这样做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政声人去后。时隔数十年,在他任职的每一个地方,当地父老乡亲仍然记着余老的好,仍然在赞颂着他。
人常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风的传承需要长辈们平时的言传身教,用自身的行为来影响下一代,一代一代继承下去,才能形成家风。从余老到同事老余,我看到了也深切感受到了良好家风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