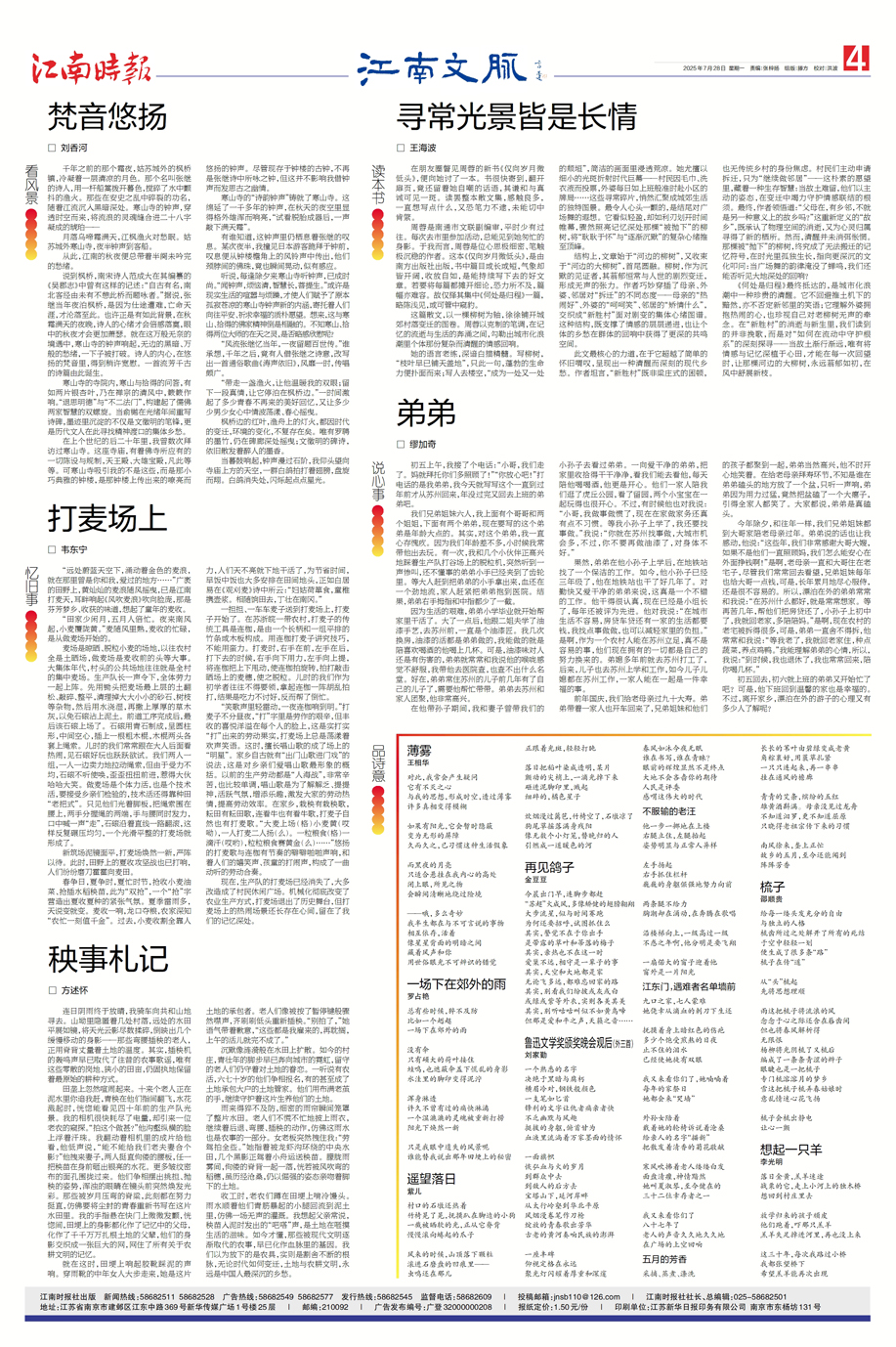秧事札记
□ 方述怀
连日阴雨终于放晴,我骑车向共和山地寻去。山坳里隐匿着几处村落,远处的水田平展如镜,将天光云影尽数揉碎,倒映出几个缓慢移动的身影——那些弯腰插秧的老人,正用脊背丈量着土地的温度。其实,插秧机的轰鸣声早已取代了往昔的农事歌谣,唯有这些零散的岗地、狭小的田亩,仍固执地保留着最原始的耕种方式。
田垄上忽然喧闹起来。十来个老人正在泥水里你追我赶,青秧在他们指间翻飞,水花溅起时,恍惚能看见四十年前的生产队光景。我的相机很快耗尽了电量,却引来一位老农的窥探。“拍这个做甚?”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浮着汗珠。我翻动着相机里的成片给他看,他低声说,“能不能给我们老夫妻合个影?”他拽来妻子,两人挺直佝偻的腰板,任一把秧苗在身前砸出银亮的水花。更多皱纹密布的面孔围拢过来。他们争相摆出挑担、抛秧的姿势,浑浊的眼睛在镜头前突然焕发光彩。那些被岁月压弯的脊梁,此刻都在努力挺直,仿佛要将尘封的青春重新书写在这片水田里。我的手指悬在快门上微微发颤,恍惚间,田埂上的身影都化作了记忆中的父母,化作了千千万万扎根土地的父辈,他们的身影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了所有关于农耕文明的记忆。
就在这时,田埂上响起胶靴踩泥的声响。穿雨靴的中年女人大步走来,她是这片土地的承包者。老人们像被按了暂停键般骤然噤声,齐刷刷低头重新插秧。“别拍了,”她语气带着歉意,“这些都是我雇来的,再耽搁,上午的活儿就完不成了。”
沉默像涟漪般在水田上扩散。如今的村庄,青壮年的脚步早已奔向城市的霓虹,留守的老人们仍守着对土地的眷恋。一听说有农活,六七十岁的他们争相报名,有的甚至成了土地承包大户的土地管家。他们用布满老茧的手,继续守护着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
雨来得猝不及防,细密的雨帘瞬间笼罩了整片水田。老人们不慌不忙地披上雨衣,继续着后退、弯腰、插秧的动作,仿佛这雨水也是农事的一部分。女老板突然拽住我:“劳驾拍全些。”她指着被龙虾沟环绕的中央水田,几个黑影正驾着小舟运送秧苗。朦胧雨雾间,佝偻的脊背一起一落,恍若被风吹弯的稻穗,虽历经沧桑,仍以倔强的姿态亲吻着脚下的土地。
收工时,老农们蹲在田埂上啃冷馒头。雨水顺着他们青筋暴起的小腿回流到泥土里,仿佛一场无声的灌溉。我想起父亲常说,秧苗入泥时发出的“吧嗒”声,是土地在咂摸生活的滋味。如今才懂,那些被现代文明逐渐取代的农事,早已化作血脉里的基因。我们以为放下的是农具,实则是割舍不断的根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土地与农耕文明,永远是中国人最深沉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