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柴
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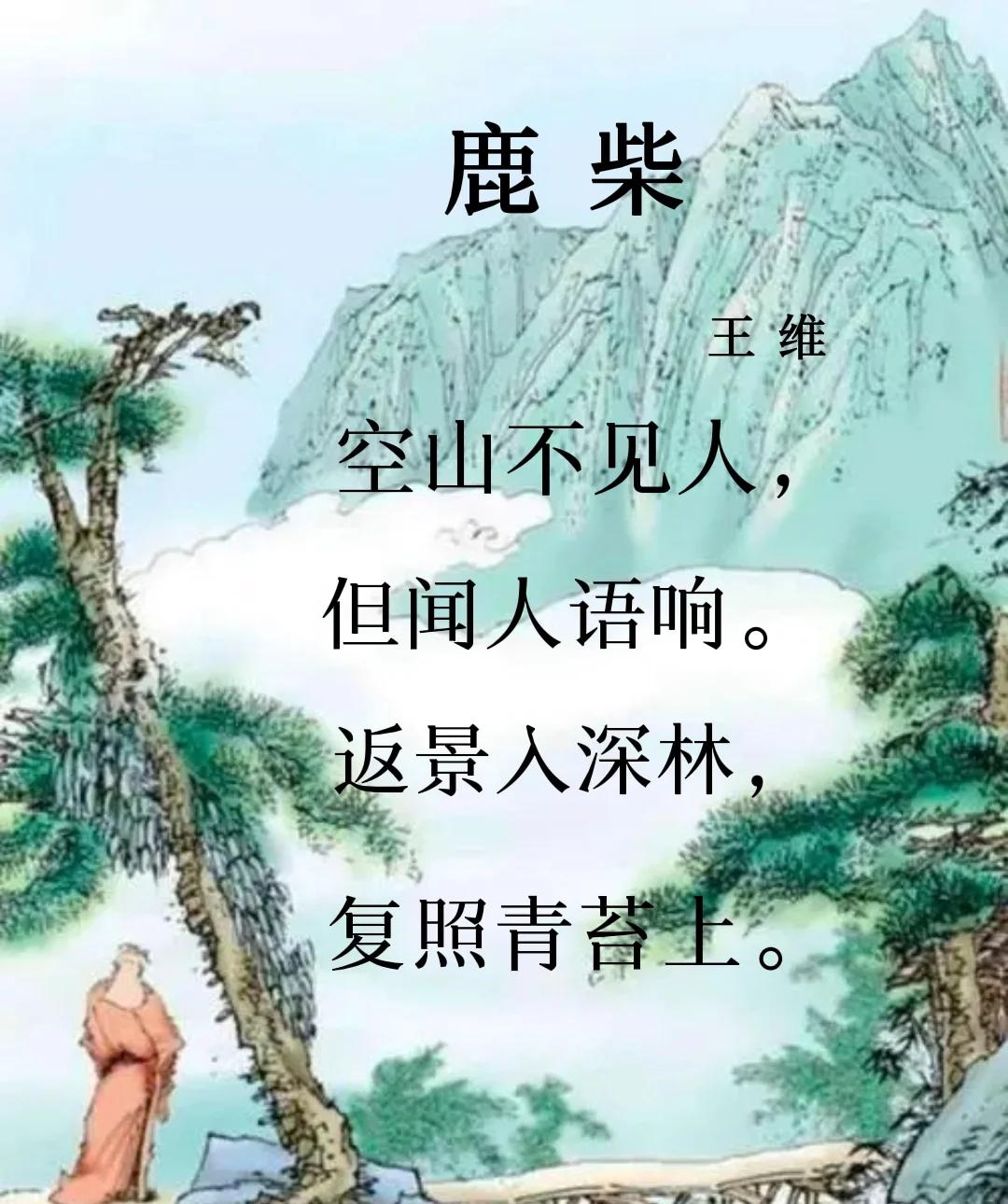
《鹿柴》是唐代诗人王维山水诗的典范之作。这首诗诗人借助对鹿柴(zhài)附近的空山深林傍晚时分的幽静景色的描绘,表达了其幽静清闲的志趣。鹿柴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南,是王维辋川别业胜景之一。
首句“空山不见人”中的主体词为“空山”,点明了地形地貌以及所在地的主体性特征。“空山”并不是空旷的童山秃岭,而是空灵静谧的山林。之所以“不见人”并非没有人,只是少有人迹,但不是与世隔绝。由“但闻人语响”可知此地正处在“有人”与“无人”的边缘带。虽然偏远,但绝不偏僻;虽然静谧,却非死寂。因此,此山虽显得“空”,却没有阴森可怖的瘆人之感。
开篇这两句,让我们想到了老子所构想的那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彼此紧邻,却互不打搅,和平而宁静。这应该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给我们的一种暗示。
“这‘人语响’,似乎是破‘寂’的,实际上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响’反衬出全局的、长久的空寂。空谷传音,愈见空谷之空;空山人语,愈见空山之寂。人语响过,空山复归于万籁俱寂的境界;而且由于刚才那一阵人语响,这时的空寂感就更加突出。”(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这是把王维笔下的“但闻人语响”,单纯当做以动衬静的技术性处理了。
假如只为突出“空山”的空旷宁静,营造出“鸟鸣山更幽”的意境,那就不如说“但闻鸟语响”或“但闻流泉响”了,这样不仅可以获得以声衬静的效果,同时还可以显示出此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美好。此地处偏僻,远离尘嚣,人迹罕至,却生气盎然。
假如诗人要表现此地幽深,反映其内心的孤独寂寞,那就选用“但闻风林响”,风吹经过树林发出的声响,不进能够营造出以声衬静的效果,还可以给人此地与世隔绝,不见人踪,更无人烟的荒远之感。但这显然与诗人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情感基调不合。
诗人之所以选择“但闻人语响”,显然表明诗人他希望疏离红尘,但又不愿意与世隔绝;他不愿受到红尘的滋扰,却又希望享受到“有人”的生气。总是,诗人自觉疏离红尘,却又不想让自己过于边缘化,这隐约让我们感到,诗人好像试图于俗世与净土之间在寻求一种平衡,反映出来的似乎是其“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人生态度。
接下来,我们看三四两句。“返景”即夕阳。“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是说傍晚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林丛杂,洒照在空山地面的青苔上。平常无奇的十个字,却绘写出一幅静谧且斑斓的山水画:一束束鲜红的夕阳,投射在苍翠碧绿的青苔上;树木向阳的一面光亮,背阳的一面幽暗,光照与色彩,共同绘制出一幅色彩斑斓、有明有暗的空山晚景图。
这一美妙的图景,不是出于诗人的想象,而是诗人眼前即时所见之实景的再现。这一景象,却似乎给我们作出了这样的暗示:夕阳西下,夜幕不久降临,牛羊纷纷返圈,倦鸟也络绎归巢,然诗人却并没有急于下山回家的意思,还依然兴致浓郁地欣赏着这空山美景,流连忘返。你不会因此觉得诗人闲情满怀?你不会因此觉得诗人对大自然的痴迷?你不会因此觉得诗人对红尘人事的淡薄?
尤其“青苔”这一意象,除了与夕阳相映成趣而外,是不是还暗示我们,此地人迹罕至?这除了与开篇的“空山不见人”照应之外,是不是还告诉我们:诗人流连之处正是他人罕至之地?这是不是暗示我们:诗人的人生趣味和价值取向与一般世人不同?这是不是与刘禹锡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人不用标榜自己有多么的不同流俗,而其不同流俗的趣味就在这“复照青苔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我们再看“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这个“复”字。其基本语义就是重又、再次的意思。这里的“复”显然在告诉我们:诗人不是一次来到此处,也不是一次见到眼前这样的景象,而是多次来过此地,反复欣赏过当前的这番美景。要不这个“复”又从何说起呢?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固然是写当前所见的实景,但其又只是简单地呈现当前实景。除了可以引发我们做出以上的种种想象和推想而外,还刺激我们作以下的一些联想:
傍晚的夕阳斜晖,可以透过茂密树林投射进来,那早晨日上三竿的时候呢?朝晖是不是也同样可以投射进这片树林?那时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而当丽日当空的中午时分呢,茂密蓊郁的树冠遮挡着阳光,那时空山密林深处又该是一片什么样的情形呢?诗人提供的这后两句的景物实写,让我们推想出一天之内不同时段,空山密林里光线明暗的变化,从而又可以获得另一个层面的审美享受……高明的诗人总是善于假托有限的文字或意象,带给读者提供更为广泛的想象或联想的空间,而且还总是显得那么的不经意。
长篇易构,断章难工。五言绝句,体制短小,容量有限,诗人就得设法在有限中蕴含丰富,在个别中蕴藏一般。其最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在有形中寄寓无形,在实有中带出无有,充分发挥利用语言文字或意象的暗示功能,从而达到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效果。
很多人只看到了诗人借助声响和光线的映衬,营造出来的“空山人语响和深林入返照的一刹那间所显示的特有的幽静境界”(《唐诗鉴赏辞典》),感受到了这首诗所带来的那种“有声的静寂和有光的幽暗”的意境美,所谓“人语响,是有声也;返景照,是有色也。写空山不从无声无色处写,偏从有声有色处写,而愈见其空”(清人李锳《诗法易简录》),而很少有人注意循着诗歌的措辞和意象,去探寻其中隐含着的诗人心迹。这种只顾“即色”“着相”,而忘却“色”“相”之下所隐藏的情意趣味的鉴赏,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诗以言志。鉴赏一首诗,只注重其艺术技法的运用和呈现出来的形迹表象,而不去洞察体会诗人内心的思想情感,不能算到位。任何一首真正的好诗,它一定是“外事造化,内得心源”的,一定是外在的物象与诗人内在情感的高度的统一。至于说王维的山水诗里所体现出来的什么“禅境”“禅意”等,却不是一般鉴赏者所能感受领略得到的,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逼迫自己去硬性搬弄这些概念术语。
古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诗人苦心构思经营,以简易平实的文字和日常易见的意象,营造出浑厚丰富的艺术意境,读者也得潜心代入,只有怀着最大的同情,才能比较充分地领略到诗人为我们营造出来的艺术境界的美好与精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