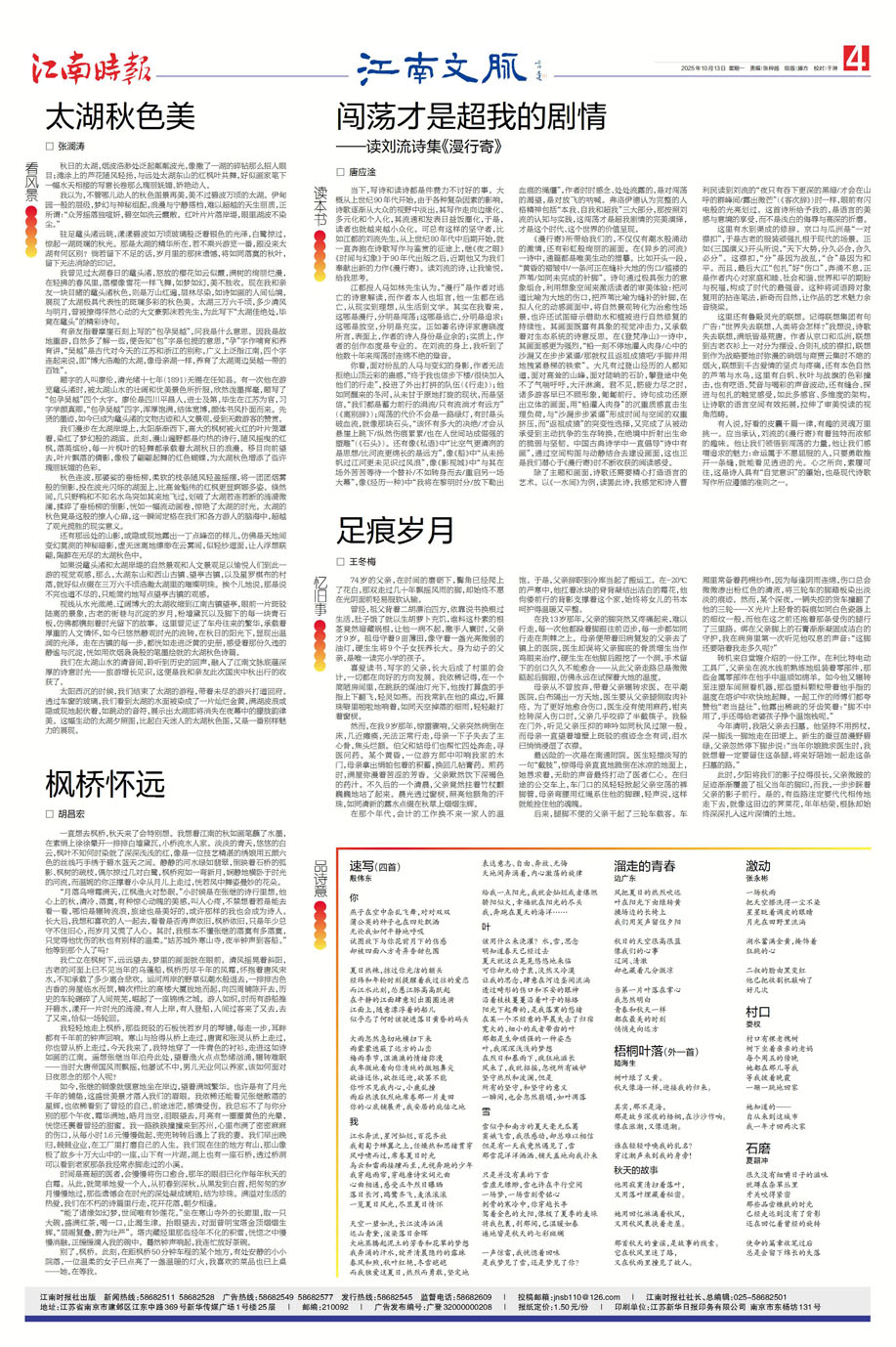足痕岁月
□ 王冬梅
74岁的父亲,在时间的磨砺下,鬓角已经爬上了花白,那双走过几十年飘摇风雨的脚,却始终不愿在光阴面前轻易服软认输。
曾经,祖父背着二胡漂泊四方,依靠说书换粮过生活,肚子饿了就以生胡萝卜充饥,谁料这朴素的根茎竟然暗藏祸根,让他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时,父亲才9岁。祖母守着9亩薄田,像守着一盏光亮微弱的油灯,硬生生将9个子女抚养长大。身为幼子的父亲,是唯一读完小学的孩子。
喜爱读书、写字的父亲,长大后成了村里的会计,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依稀记得,在一个简陋房间里,在跳跃的煤油灯光下,他拨打算盘的手指上下翻飞,轻灵如燕。而我常趴在他的桌边,听算珠噼里啪啦地响着,如同天空掉落的细雨,轻轻敲打着窗棂。
然而,在我9岁那年,惊雷骤响,父亲突然病倒在床,几近瘫痪,无法正常行走,母亲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焦头烂额。伯父和姑母们也帮忙四处奔走,寻医问药。某个黄昏,一位游方郎中叩响我家的木门,母亲拿出绢帕包着的积蓄,换回几帖膏药。煎药时,满屋弥漫着苦涩的芳香。父亲默然饮下深褐色的药汁。不久后的一个清晨,父亲竟然拄着竹杖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晨光透过窗棂,照亮他额角的汗珠,如同清新的露水点缀在秋草上熠熠生辉。
在那个年代,会计的工作换不来一家人的温饱。于是,父亲辞职到冷库当起了搬运工。在-20℃的严寒中,他扛着冰块的脊背凝结出洁白的霜花,他佝偻前行的背影支撑着这个家,始终将女儿的书本呵护得温暖又平整。
在我13岁那年,父亲的脚突然又疼痛起来,难以行走,每一次他都跺着脚跟往前迈步,每一步都如同行走在荆棘之上。母亲便带着旧病复发的父亲去了镇上的医院,医生却误将父亲脚底的骨质增生当作鸡眼来治疗,硬生生在他脚后跟挖了一个洞,手术留下的创口久久不能愈合——从此父亲走路总是微微踮起后脚跟,仿佛永远在试探着大地的温度。
母亲从不曾放弃,带着父亲辗转求医。在平潮医院,白布隔出一方天地,医生要从父亲腿侧取肉补疮。为了更好地愈合伤口,医生没有使用麻药,钳夹捻转深入伤口时,父亲几乎咬碎了半截筷子。我躲在门外,听见父亲压抑的呻吟如同秋风过隙一般。而母亲一直望着墙壁上斑驳的痕迹念念有词,泪水已悄悄浸湿了衣襟。
最凶险的一次是在南通附院。医生轻描淡写的一句“截肢”,惊得母亲直直地跪倒在冰凉的地面上,她恳求着,无助的声音最终打动了医者仁心。在归途的公交车上,车门口的风轻轻掀起父亲空荡的裤脚管,母亲弯腰用红绳系住他的脚踝,轻声说,这样就能拴住他的魂魄。
后来,腿脚不便的父亲干起了三轮车载客。车厢里常备着药棉纱布,因为每逢阴雨连绵,伤口总会微微渗出粉红色的清液,将三轮车的脚踏板染出淡淡的痕迹。然而,某个深夜,一辆失控的货车撞翻了他的三轮——X光片上胫骨的裂痕如同白色瓷器上的细纹一般,而他在这之前还拖着那条受伤的腿行了三里路。绑在父亲脚上的石膏渐渐凝固成洁白的守护,我在病房里第一次听见他叹息的声音:“这脚还要陪着我走多久呢?”
转机来自堂嫂介绍的一份工作。在利比特电动工具厂,父亲坐在流水线前熟练地组装着零部件,那些金属零部件在他手中温顺如绵羊。如今他又辗转至注塑车间照看机器,那些塑料颗粒带着他手指的温度在熔炉中欢快地起舞。一起工作的师傅们都夸赞他“老当益壮”,他露出稀疏的牙齿笑着:“脚不中用了,手还得给老婆孩子挣个温饱钱呢。”
今年清明,我陪父亲去扫墓。他坚持不用拐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新生的蚕豆苗漫野碧绿,父亲忽然停下脚步说:“当年你娘跪求医生时,我就想着一定要留住这条腿,将来好陪她一起走这条扫墓的路。”
此时,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父亲微跛的足迹渐渐覆盖了祖父当年的脚印,而我,一步步踩着父亲的影子前行。是的,有些路注定要代代相传地走下去,就像这田边的荠菜花,年年枯荣,根脉却始终深深扎入这片深情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