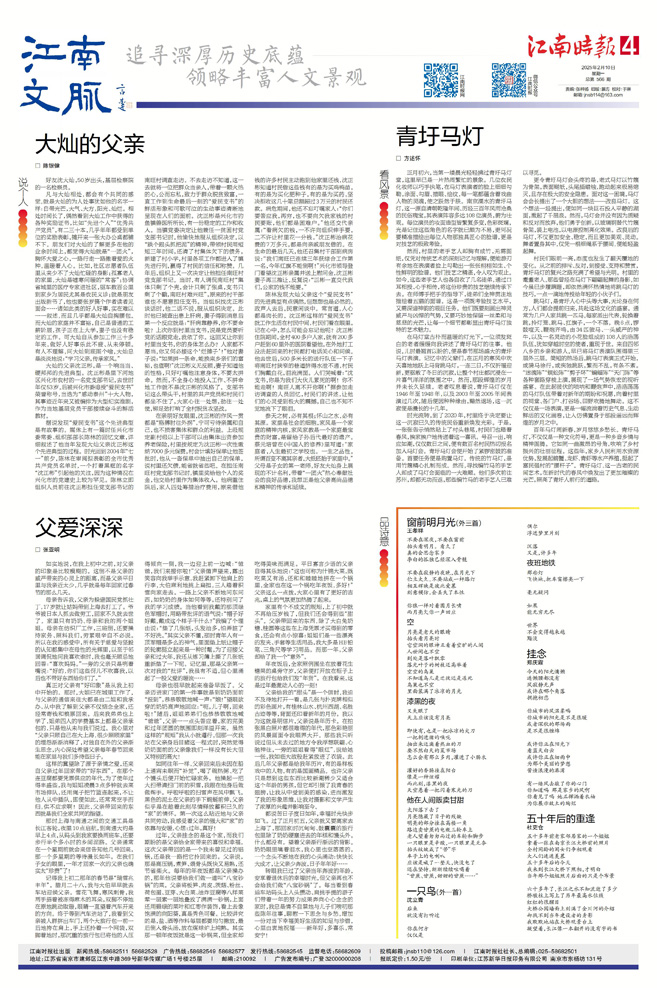父爱深深
□ 张亚明
如实地说,在我上初中之前,对父亲的印象是比较模糊的。这倒不是父亲的威严带来的心灵上的距离,而是父亲平日里与我亲近太少,几乎就是每年回家过春节的那么几天。
母亲告诉我,父亲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17岁就让姑妈带到上海去打工了。爷爷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回家不久就去世了。家里只有奶奶、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母亲在纺织厂工作,三班倒,还要操持家务、照料我们,劳累艰辛自不必说。所以在我的感受中,所有关于慈爱与坚毅的认知都集中在母性的光辉里,以至于邻居调侃地问我喜欢谁时,我也毫无顾忌地回答:“喜欢妈妈。”一旁的父亲只是咧着嘴说:“好的,你们这些伢儿不欢喜我,以后也不带好东西给你们了。”
真正对父亲有“好印象”是从我上初中开始的。那时,大姐已在城里工作了,与父亲的通信来往大都是由二姐和我承办,从中我了解到父亲不仅惦念全家,还经常寄钱和粮票回来。后来我弟弟也上学了,姐弟四人的学费基本上都是父亲承包的,只是他从未与我们说过。我心里对“父亲只顾自己在大上海,很少照顾家里”的埋怨渐渐消释了,对独自在外的父亲渐生思念,内心深处希望父亲每年春节回来能在家里与我们多待些日子。
这样的冀望除了源于亲情之爱,还来自父亲过年回家带的“好东西”。在那个连豆腐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为了使年过得丰盛些,我与姐姐凌晨3点多钟就去菜市场排队,还用绳子把竹篮连起来,不让他人从中插队,即便如此,还常常空手而归,供不应求啊!因此,父亲带回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全家共同的指望。
那时上海与南通之间的交通工具是长江客轮,夜里10点启航,到南通大约是早上4点,从码头到我家要换两班车,还要步行半个多小时的乡间泥路。父亲通常在一个星期前就会来信告知他几号回来,那一个多星期的等待漫长如年。在我们子女的眼里,一年才回家一次的父亲也确实太“珍贵”了!
记得我上初二那年的春节是“瑞雪兆丰年”。腊月二十八,我与大伯早早就去车站迎候父亲。雪花飞舞,寒风刺骨,我两手捂着被冻得麻木的耳朵,双脚不停地在原地跳动取暖,眼睛一直望着汽车开来的方向。终于等到汽车进站了,我看到父亲被人群挤出车门,两个大旅行包一前一后地挎在肩上,手上还拎着一个网袋,双脚着地时,那沉重的旅行包已将他的人压得倾向一侧,我一边迎上前一边喊:“爸爸,我们来接你啦!”父亲循声望来,露出笑容向我举手示意,我赶紧卸下他肩上的行李,大伯麻利地挑上扁担,三人踏着积雪向家走去。一路上父亲不断地问东问西,如奶奶的身体如何等等,还特别问了我的学习成绩。当他看到我戴的那顶绿色军帽时,用略带批评的语气说:“帽子好好戴,戴成这个样子干什么?”我编了个理由说:“垫了几张纸,头发油多,怕弄脏了不好洗。”其实父亲不懂,那时青年人有一顶军帽是多么的神气,里面垫上纸让帽子的轮廓挺立起来是一种时髦,为了迎接父亲和过大年,我还从练习簿上撕了几张纸重新垫了一下呢。记忆里,那是父亲第一次对我的“批评”,我虽有不适,但心里涌起了一股父爱的暖流……
母亲也很早就起来准备早饭了。父亲迈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奶奶面前“报到”,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娘!”望眼欲穿的奶奶高声地回应:“呃,儿子啊,回来啦!”随后,姐姐弟弟们也恭恭敬敬地喊“爸爸”,父亲一一点头答应着,家的完美和过年团圆的氛围即刻洋溢开来。虽然这样的“规矩”我从小就遵行,但那一次我站在父亲身后目睹这一程式时,突然觉得奶奶面前的父亲像我们一样没有长大但又特别的高大!
如同往年一样,父亲回来后未因在船上通宵未眠而“补觉”,喝了碗热粥、吃了个馒头后便开始忙碌家务。他操起一把大扫帚清扫门前的积雪,我跟在他身后做做帮手。呼啦呼啦的扫雪声在风中飘飞,黑色的泥土在父亲的手下蜿蜒前伸,父亲似乎是在趁着此刻尽情释放蓄积已久的“家”的情怀。第一次这么贴近地与父亲共同劳动,我感受着父亲的强大和“家”的依靠与安暖,心想:过年,真好!
过年,父亲挂念的是这个家,而我们期盼的是父亲给全家带来的喜悦和幸福。这次父亲带回的是一个我未曾见过的铝锅,还是我一路把它拎回来的。父亲说,那是高压锅,煮笋、煨骨头既快又易熟,还节省柴火。每年的年夜饭都是父亲操办的,那年他说要给我们做一道叫“八宝砂锅”的菜。父亲将板笋、肉皮、茨菇、粉丝、荷包蛋、豆芽、大白菜、油炸豆腐等八样菜荤一层素一层地叠放了满满一砂锅,上面还用碧绿的菜叶和红枣作装饰,看上去像饱满的向阳葵,真是秀色可餐。比较讲究的是,盐、酒等作料每层都要均匀撒放,最后倒入骨头汤,放在煤球炉上炖熟。其实那一顿年夜饭就是这一砂锅菜,但全家却吃得美味而满足。平日寡言少语的父亲自得其乐地说:“这也可称为什锦大菜,既吃菜又有汤,还和和睦睦地拼在一个锅里,全家也在这一个锅吃年夜饭,多好!”父亲这么一点拨,大家心里有了更好的吉兆,桌上的气氛更加热腾了起来。
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了初中就不再给压岁钱了,但我们还会得到些“甜头”。父亲带回来的东西,除了大白兔奶糖、桂圆等这些在上海凭票才买得到的零食,还会有点小惊喜:姐姐们是一些漂亮的发夹、手套等生活用品,我大多是HB铅笔、三角尺等学习用品。而那一年,父亲却给了我一个“意外”。
年夜饭后,全家照例围坐在放着花生糖果的桌旁守岁,父亲便打开放在柜子上的旅行包给我们发“年货”。在我看来,这是过年最激动人心的一刻!
父亲给我的“甜头”是一个信封,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是几张与扑克牌相似的彩色画片,有桂林山水、杭州西湖、名胜古迹等等,背面还印着新年的月份。我以为这就是明信片,父亲说是年历卡。在拍张黑白照片都很难得的年代,那色彩艳丽的风景画面令我眼界大开。那些我只听说过但从未去过的地方令我浮想联翩、心驰神往,一旁的姐姐看得“眼红”,说给她一张,我如临大敌般赶紧放进了衣袋。此后几年父亲都是给我年历片,有的是样板戏中的人物,有的是国画精品。也许父亲只是想到这些东西比较新潮稀少又适合这个年龄的男孩,但它却引振了我青春的翅膀,让我从中受到美的感染,进而激发了我的形象思维,让我对摄影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影响至今。
都说苦日子度日如年,幸福时光快步如飞。过了正月初五,父亲就又要离家去上海了,那回家时沉甸甸、鼓囊囊的旅行包里除了奶奶硬塞进去的年糕和馒头外,什么都没有。望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奶奶眼里噙着泪水,我心里也空落落的,一个念头不断地在我的心头涌动:快快长大成才,让父亲少奔波,日子年年好……
转眼我已过了父亲当年奔波的年龄,安享着退休后的幸福时光,但父亲再也不会给我们做“八宝砂锅”了。每当看到春运车站码头上人头攒动、肩挑手提的游子们带着一年的努力成果奔向心心念念的家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与儿子们唠叨那些陈年往事,聊慰一下思念与乡愁,增加一份对当下幸福美好生活的知足与珍惜,心里由衷地祝福——新年好,多喜乐,常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