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很有感慨,很受启发。组织者经过反复考量,把这四位作家的作品集中起来,进行研讨,是一种展示,是一次亮相,也是一次比较,一次把脉。大家的发言都很精辟深入,较少浮语虚辞,较少大而不当,较少肉麻吹捧,较少言不及义,较少隔靴搔痒。《跪向土地》,多少年前,听已故的小说家、出版人黄孝阳说到过。邹雷的《生命的燃烧》,是我推荐给有关出版机构得以刊行的。据会议组织者的分工,我在会前看的是周淑娟的《贾汪真旺》《大河奋辑》。时间有限,只能简略说一些一己之见,贻笑大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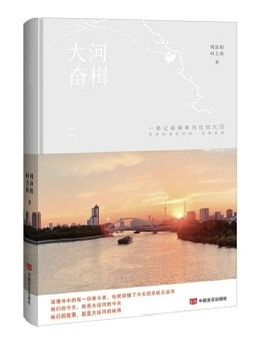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似乎遭遇了严重危机,有人主张以非虚构这一称谓取而代之。也有“聪明”的人说,高人写小说,异人写诗歌,完人写散文,至于何人写报告文学,似乎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散文的门槛低,是不争的事实。报告文学的名声不尽如人意,或者说声名狼藉,多有议论,也并非空穴来风。丁晓原老师是研究报告文学的权威,有多种专著,影响巨大。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时间并不太久,应该是脱胎于新闻纪实。多年前,编选报告文学选本,也还有加上纪实、特写的称谓。问题来了,因这一文体的新闻性或者说时代性、当下性,他是时代的近距离反应,他是众人瞩目的重大问题的后新闻记述,他是紧贴时代律动的“轻骑兵”,把握得好,让人激赏;但若把握不好,则会吃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成为一种易碎品,甚至给写作者带来一定的尴尬与难堪。山海关外,辽东半岛,有一座城市,历史虽不悠久,经历却多沧桑,120年前的日俄战争就是在此打响,也有以此为背景的俄罗斯人的文本,曾引发争论,酿成风波。我不是说外国人的文本,是说一报告文学作家书写这一城市,过多的夸张宣扬当时主政者的“丰功伟绩”,而这一主政者后来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这一曾经炙手可热的文字书写顿然间陷入令人讶异的沉默失语之中。这样的教训很多,不胜枚举。当然,不能因这一文体的固有特点而因噎废食,以偏概全。但,这样的教训还是应该汲取反省,不能率尔操觚,不能头脑发热,不能轻浮冲动,不能罔顾职业尊严而肆意妄为、胡为、乱为。就大运河而言,一段时间以来,似乎很热,滚烫发烧。要说明的是,远在大运河没有热起来之前,夏坚勇就写了《大运河传》,他书写大运河,也可看作是他“宋史三部曲”的一种预热,一种练笔,一种准备。周淑娟与何圭襄的《大河奋辑》无意为大运河作传,他们聚焦江苏境内的大运河两岸的八座城市,但也不是去全面反映这八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不是有人写有大运河两岸的21座城市吗?他们撷取选择这八座城市中最为普通的人,反映他们的当下生活状态,一人一城,自南到北,逶迤而来,都是小人物,遍布五行八作,有开民宿的,有搞旅游的,有从事砚台这一古老技艺的,有继承乱真绣这一非遗的,有斫琴的,有搞摄影作播客的,有作花木售卖的,还有在电力公司上班参加过当年九江抗洪抢险的,林林总总,色彩缤纷,因为一条河,把他们串联起来,把他们展示出来,成为一水两岸人间烟火的代表性人物,向我们一一走来,活泛,生动,元气淋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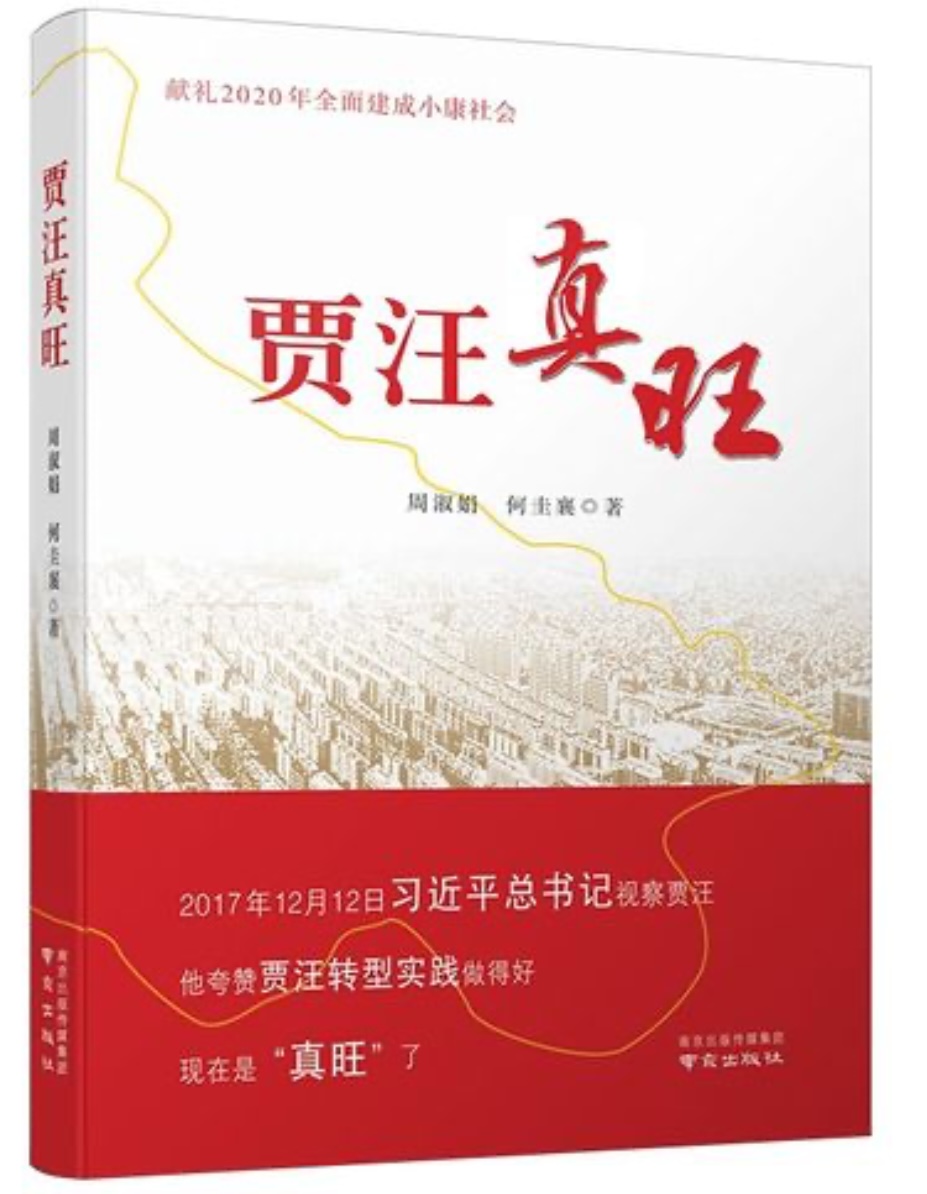
需要说明的是,运河热度不减,各种文本次第而来,其间鱼龙混杂张冠李戴者也有不少,其间望文生义闭门造车凭空想象者也并不少见。周淑娟何圭襄不去纠缠大运河的是是非非,不过多描绘这些城市的如烟往事历史苍茫,即使叙说这些城市的历史人文,也多是为当下人物服务,如其中写常州杨守玉,她与刘海粟的故事,令人动魄惊心。艾青似乎也在这座城市读书留下过痕迹?说到宿迁,他们提到一位名叫胡琏的人,不是民国的将军胡琏,是吴承恩的舅舅胡琏,说到茶艺,他们也提到陆羽的《茶经》,他们节制而舒缓,从容而内敛,已经不是好人好事层面上的廉价讴歌,不是蜻蜓点水的新闻报道式的本报讯。在审视拿捏操笔行文之时,他们字斟句酌,他们精雕细琢,即使征引《漂海录》《砚史》,也没有囫囵吞枣,汪洋恣肆。应该说,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语言呈现,读者都能感受到他们从《贾汪真旺》到《大河奋辑》的巨大进步与跃升,真是迂回曲折说当下,娓娓道来写烟火,细细打磨有讲究。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有人说文学多了,报告少了,也许有一定道理。报告需要深入细致,需要仆仆风尘,需要走得进去又能站得出来,看拉铁摩尔写中国长城,看奥登的《战地纪行》,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林放的《延安一月》,这样的报告,这样的锐利,需要敏锐观察,需要涵咏吸纳,需要沉潜磨勘,哪能一蹴而就酣畅淋漓?心中无底,浮于表面,也只能是靠所谓文学来粉饰涂抹作为油彩了。但也有人说,不是报告多少的问题,是有无文学的问题。报告文学因其时代性、主题性、当下性、时效性,被误认为可以公文化、可以急就章、可以萝卜快了不洗泥,要献礼啊,要赶工期啊,要按照月份牌踩准节奏啊,如此这般,只能是公文化、塑料化,没有生机,没有活力,实际上连起码的文从字顺都要大打折扣,这样的所谓文学报告,又怎能受人待见不被弃之如敝屣呢?

周淑娟笔下的一水,自然是大运河;他们说哪八座城市?他们说的是苏州、无锡的宜兴、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宿迁,落脚点是他们如今生活的徐州,江苏的北大门。听闻,周淑娟何圭襄夫妇正在创作的《到震泽》,收官在即。汪,河,泽,都是水,是他们的河水三部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