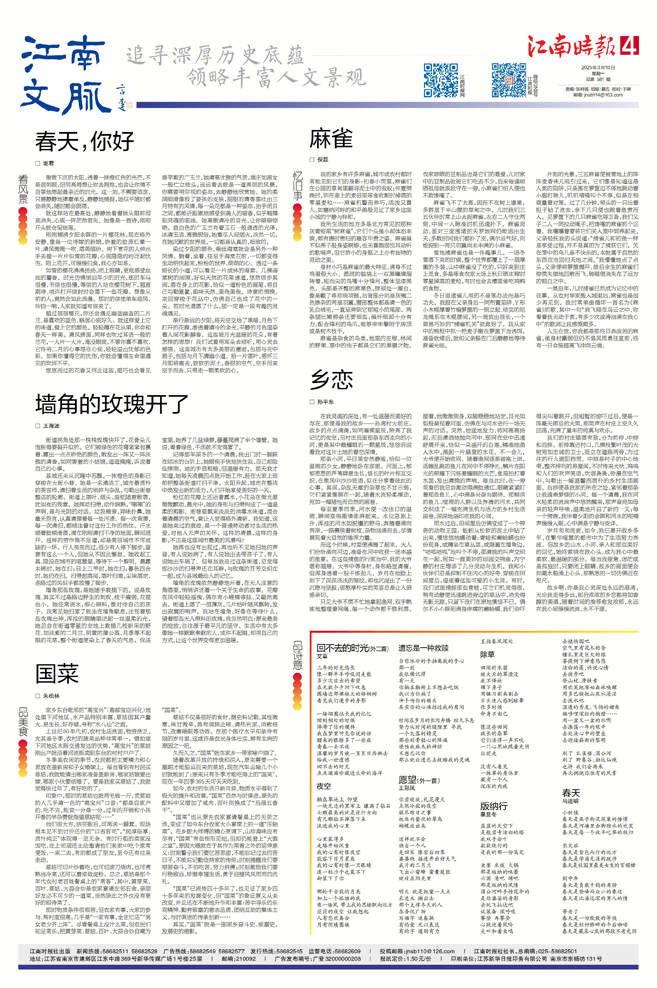麻雀
□ 倪磊
我的家乡有许多麻雀,城市或农村都时常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初春小雨里,麻雀们在公园的草甸里翻寻泥土中的虫蚁;仲夏傍晚时,则在垄上的麦田里啄食收割时掉落的零星麦粒……麻雀机警而乖巧,活泼又喜人,如塞纳河畔的和平鸽般见证了家乡这座小城的宁静与祥和。
我所生活的地方多是北方常见的那种灰黄短尾“树麻雀”,它们个头虽小却体态丰腴,颇有唐时贵妇的雍容华贵之姿。麻雀虽不似燕子般身姿婀娜,也无喜鹊那悦耳动听的歌唱声,但它娇小的身躯之上亦有独特的灵动之美。
身材小巧是麻雀的最大特征,通身不过鸡蛋般大小。圆润的脑袋上一双黑瞳滴溜转着,短而尖的鸟嘴十分锋利,整体呈漆黑色。头部是齐整的麻栗色,脖颈处一圈白,像是戴了串珍珠项链,后背部分则是灰褐二色掺杂的两扇羽翼,腹部整体都是清一色的乳白绒毛,一直延伸到它那短小的尾部。两条腿比嫩柳条还要细些,虽纤细却十分有力,配合锋利的鸟爪,能够牢牢攀附于房顶或是树木枝干。
麻雀是杂食的鸟类,地里的庄稼、林间的野果、草中的虫子都是它们的果腹之物。农家晾晒的豆制品也是它们的最爱,儿时家中的豆制品就被它们吃去不少,后来每逢晾晒祖母就派我守在一旁,小麻雀们怕人便也不敢馋嘴了。
麻雀飞不了太高,因而不在树上建巢,多群居于半山腰的草甸之中。儿时我们三五伙伴时常上山去捉麻雀,左右二人守住两侧,中间一人瞅准时机迅速扑下。麻雀灵动,面对三面围堵的天罗地网仍能逃出生天,多数时间我们都扑了空,偶尔运气好,则能捉到一两只羽翼尚未丰满的小麻雀。
雪地捕麻雀也是一件趣事儿。一场冬雪落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覆上了一层厚重的冬装,山中麻雀没了吃的,只好来到庄上觅食,多是啄食农家大场上秋日晒庄稼时零星掉落的麦粒,有时也会去槽里偷吃鸡鸭的食物。
冬日里逮雀儿用的不是笨办法而是巧功夫。我跟在父亲身后一同布置陷阱,Y形小木棍撑着竹编箩筐的一侧立起,结实的尼龙绳系在木棍腰间,另一端放出很长,一个简易巧妙的“捕雀机关”就做好了。我从家中的粮柜中抓一把麦子撒在箩筐下当诱饵,准备就绪后,就和父亲躲在门后静静地等待麻雀光临。
片刻的光景,三五麻雀便被雪地上的阵阵麦香味儿吸引过来。它们像是知道这是人类的陷阱,只是围在箩筐边不停地跳动着小脚打转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似是互相商量着对策。过了几分钟,领头的一只壮着胆子钻了进去,余下几只便也跟着鱼贯而入。见箩筐下的几只麻雀吃得正香,我们父子二人一同拉动绳子,把馋嘴的麻雀抓个正着。我嚷嚷着要将它们关入笼中饲养起来,父亲轻抚我的头说道:“捕雀儿和钓鱼一样是享受过程,并不是真的为了捕获它们。关在笼中的鸟儿是不快乐的,本就属于自然的东西应当回归天地之间。”我懵懂地点了点头,父亲便将箩筐揭开,劫后余生的麻雀们惊慌失措地四散而飞,转眼便消失在了远方的银白之中。
一晃经年,儿时捕雀已然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从农村举家搬入城里后,麻雀也是很少再见到。我时常单曲循环一首名为《麻雀》的歌,其中一句“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的歌词让我感慨颇多。
人生在世,你我都是那终日奔波苦的麻雀,虽身材羸弱但仍不惧风雨勇往直前,终有一日会振翅高飞冲向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