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新闻战线上的著名才子、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处原书记、作家、诗人、书法家、收藏家。
笔者想起邓拓的名字,就连带地想起他跟一件国宝级文物有关的故事,不停地在我脑海的记忆中翻转起来,这便是邓拓和苏轼传世绘画真迹《潇湘竹石图卷》。这不仅仅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这还是邓拓同志爱国情怀的一则生动写照!
慧眼独具识珍宝
1961年,是我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年。这年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北京东交民巷不远处的四合院胡同巷口,有个面目清癯、 衣衫褴褛、个头高挑,被凛冽的寒风吹得瑟瑟发抖的年近古稀的老者,手抱带轴画卷,一动不动地低着头伫立在那里,时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快速地扫视着在他身旁走过的行人。
随着“嘀嘀”两声鸣响,一辆苏式伏尔加轿车,在老人伫立的地方戛然而止。
从车里走出来一位风度翩翩、举止文雅约莫50岁左右的男子,颇有礼貌地迎上前去向伫立者招呼道:老人家,您手里拿的是什么宝贝啊,可不可以让我看看呢?
老人见轿车停在身旁,便觉问者不是一般人,揣摩着这人可能还是个大官。
于是他非常客气地展开画卷,向问者介绍道:这是我家的传家宝,一幅宋代名人的山水画卷,不知在我家传了多少代人了?
老者揉了揉湿润的眼睛,沮丧地望着问者说:近来家中揭不开锅,实在没有办法可想,想把它变现保命。
问者对老者表示十分同情,就半隐瞒自己的身份说道:我姓邓,是北京市委普通工作人员(其时的邓拓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我想买您的这幅画,让我把画再认真地看一会可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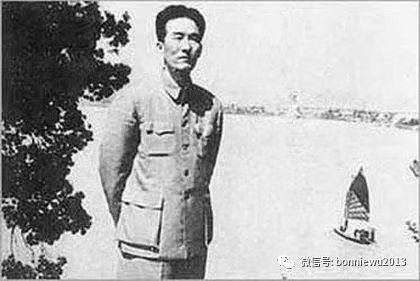
此时老者如同见到救星一般,按耐不住喜形于色地说:随便看,您看多长时间都成,只要您诚心想买。
邓拓看见画作装裱素雅古朴,展开的画面上一片开阔的土坡,两块石头加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氤氲缭绕,景色苍茫,与苏轼生前喜爱描绘潇湘情景极为相似,具有较高的吻合度与辨识度。邓拓凭着他自己的眼力,加深厚的书画文史功底,初步断定这可能就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书画家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若是真迹的话,它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国宝级珍品,具有很高的文物文献价值。
邓拓本就是苏轼诗文、书画的研究迷,他根据史料介绍,苏轼传世绘画作品极少,已知仅有两卷:《枯木怪石图卷》在日本藏家手里,《潇湘竹石图卷》被国内民间人士收藏,不知花落谁家,今日有缘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邓拓初步认定这是国内苏轼真迹孤品画作后,他把欣喜若狂的激动与兴奋,统统掩藏于心底,一股邂逅美遇感,在他心头如同涌动的乐泉一般流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邓拓的初步认定,正如他后来所言:当时起码有95%以上的认定把握,好像苏东坡就在他身旁告诉他似的:算你有眼力,没错,这就是我的真迹画作《潇湘竹石图卷》。
邓拓见宝心动,一时竟忘记了询问持画老人是何姓氏,他不免带有点歉意地说:老人家,对不起您哦,我光顾欣赏画卷,到现在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老人说:免贵,我姓白,您就叫我老白吧。
邓拓嘿嘿笑出声来:我今年48岁,看您是我父辈的年岁模样,我应该尊称您为白老先生才是,回去莫忘记代我向您的家人问好。
面对这个没有一点官架子、又礼近于人的邓姓干部,持画的白老先生被感动的不知说啥是好,他只说:我把传家宝卖给你这样知书达礼的人,相信您会万分爱惜它、守护它的,到了您家就像在我家一样世代珍藏它!
邓拓也被感动了,他紧紧地握住白老先生的手说:既然我与您的传家宝今日结了缘分,那就请您开个价钱吧,我决定买了,真的诚心买。
只见白老先生抖索着嘴巴,几次欲想开口讲话,但又都闭合了双唇,始终没有发出一个字的音来。
他是不是不想卖画了,还是另有隐情呢?
邓拓一时猜摸不透白老先生此刻心里在犹豫什么,于是就试探着说:若不为了度过时下生活难关,谁会把这传家古董,轻易出手卖给他人,怕是连我自己也难以做到的吧?
哪知邓拓的试探是非常有效的。白老先生用力叹了口气说:邓干部啊,您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也是书香门第的人家,祖上出过进士,哪知现如今贫困潦倒要出卖传家宝求活命的地步,老祖宗有知,定会责骂我是无能之辈,不肖子孙。可是为了活命,我有啥法子呢?思来想去,家徒四壁,能值点钱的就是这幅祖传的古画,我们全家老小眼巴巴的指望它能救命啊!
白老先生说着动了情,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话语间伴着哽咽:邓干部,您是个大忙人,我不能再犹豫不决了,那会耽误您的工作,我直说了,您出5000块钱,从此这幅画就归您所有了。
对于白老先生的开价,邓拓没有还价,在他认为这幅画若是自己初步认定的苏轼画作真迹,本就是无价之宝,何止是买卖双方以5000元成交的价格?
然而,那时5000块钱对于个人而言,不要说在60年代初,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那也是个很大的数字了,几乎没有人能够一下子拿得出来,这其中包括当时行政级别比较高的邓拓。

邓拓再一次握紧白老先生的手说:我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容我想想办法,凑足5000块钱,再买您的这幅家传古董的画可以吗?
那我怎样才能相信您的话呢?白老先生心生疑虑地说:我等不及哦,我们全家急需这笔救命钱。
邓拓摸了摸了自己的脑门,沉思了片刻:白老先生,我跟您商研,分两步走:今天我身边只有60元现金,您拿回去先用这钱买粮食,让你全家人把饭碗端起来,不至于饿坏了身体;第二步呢,这幅画您今天还是自己带回去自己保管,三日后我们此地此时不变,一手交钱,一手取画,不见不散。
白老先生对眼前这位礼先于人、又和蔼可亲的邓干部,通过短暂的接触和交谈,感觉他是个靠谱的人,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感,便点头答应了他的两步法。
那天分别时,白老先生再次重复了邓拓的那句话:三日后我们还是此地此时不变,不见不散!
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邓拓和白老先生谈妥买卖事宜分别后,回办公室看了会文件,批阅了一些职责范围内的书面材料,抬起手腕,看到手表的指针已指在下午5点的下班时间上。
多年来邓拓一直有推迟下班的习惯,可是今天他要破例——到点回家。于是,他电话通知司机马上就送他回家。
司机不信自己的耳朵,他来到邓拓办公室迟疑地问道:首长,您让我马上就送你回家?是的,马上就走。邓拓满脸微笑着回答司机。
一贯严肃的邓拓,让他的司机看到他这般“反常”的表情,便在心里嘀咕、猜测着,首长可能今天遇到什么大喜事了,要不他的心情,咋会一下子就变的这样好呢?虽然不好随便问他喜从何来,但司机认为,首长高兴他就高兴,愿他天天这样愉快多好呀。
司机猜的没错,邓拓今天确实遇到了大喜事。
邓拓下午与另一位司机因公办事途中,惊奇地发现流落在民间的苏轼绘画孤品潇湘竹石图卷,虽成交但画还没到他本人手中,如若能在三日内凑够5000元,这件国宝级文物就会成为他心爱的收藏品。
回到家中的邓拓,夫人丁一岚见他喜笑颜开的样子,就定睛地看了他一会说:你今天有啥喜事啊?为什么这样高兴呢?说来听听,让我分享分享你的喜事。
喜事当然是有的,而且弄不好还是个惊天动地的大喜事。邓拓似乎有把握地开始向他的夫人暗示:今天我们一家人推迟点时间吃晚饭,我马上到书房里查会资料,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向你和孩子们宣布,今天我有了重大发现,真的,我不骗你的!
邓拓的夫人丁一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原名叫刘孝思,参加革命工作改用他名,后来他名作真名,一直用到她1998年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
丁一岚要邓拓抓紧时间去查资料,等会要和放学回来的孩子们听他发布好消息。
在书房里,邓拓把能够找到的有关苏轼书法、绘画资料,一本一册从书橱里找到。他是苏东坡的诗书画研究迷,这些资料他之前看过多遍,放在哪里,心里有数,不一会就找齐了。
加之他今日的心情已被重大发现所愉悦,资料又找的顺手,嘴巴里情不自禁哼起了他老家福建的民间小曲《采茶歌》,哼的很有乡愁记忆的味道,他自己也感觉挺快乐的。
收藏不仅是邓拓的爱好,在其时京城收藏圈内,他还是个颇有影响的收藏家,许多人不知道他还熟稔于鉴定,古代书画,瓶瓶碗碗,坛坛罐罐,他都能凭借自己积累的鉴赏知识,常常慧眼识珠,淘到真品,所以他家里的藏品是很多的,真可谓藏锋敛锷,不露声色,鲜为人知。
邓拓的瞬间记忆力是超人的,他就凭自己下午看到的那幅苏轼绘画作品,记下诸多过目不忘的细节。

根据细节,他对照资料,先从苏轼绘画的印章开始比对。苏轼是步入中年后开始作画的,因此,邓拓认为苏轼这幅画极有可能在公元1080~1084这4年间创作产生的,也就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宋神宗赵顼贬谪黄州期间创作的。那么他的印章应该是篆书“翰林处士苏氏子瞻”和“轼为莘老作”款印,非常吻合,对上了;邓拓接着比对“竹若紫凤回风,石如白云出岫”题款,看字迹是不是苏轼丰腴、略扁、舒展、遒媚的风格,加参苏轼著名的《黄州寒食帖》、《江上帖》等真迹拓本字帖,又对上了,这正是苏轼的独家笔锋再现;邓拓最后统览印象中的整体画面,如能比对得上苏轼的尚简、尚意、超然、求趣的文人画风格,这也基本对上了。画面上200多字的长文题款诗句,是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所题。至此,这幅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邓拓完成印象鉴定,感觉甚好!
兴奋得欲罢不能的邓拓,从书房里走出来,大声对夫人说:一岚啊,孩子们都回来没有啊?你今晚多加两道菜,陪我喝一杯酒,你和孩子们要好好地为我庆贺,我今天活的太值得了。
经过我刚才的考证,我发现了苏轼的孤品绘画真迹《潇湘竹石图卷》,鉴于苏轼在北宋文化文学界的崇高地位,他传世极少的绘画真迹,堪称我们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珍宝!
邓拓正跟夫人兴奋不已地说着,上学的几个孩子都回来了,他招呼孩子们一起坐下开始晚餐。餐桌上,邓拓向全家人公布了他的重大发现,夫人和孩子们都为他祝福。邓拓由于高兴,酒量一般的他,那天起码半斤酒下了肚,脸红的像关公,兴奋得像竹林七贤里的刘伶。
一家人都为邓拓发现苏轼绘画真迹而高兴,这般其乐融融的晚餐,在邓家胜过一切的往常!可以说从没有过的、如同欢乐海洋一般难忘的晚餐!
到哪里去筹集5000元
然而,激动兴奋过后,恢复常态的邓拓,脸上的晴天慢慢地愁云遮挡和密布。
因为他先前问过夫人家里现在有多少现金,丁一岚如实告知,千元不足,就算一千元吧,还有四千元缺口,到哪去借呢?再说困难时期,大家都穷,谁还有多余的钱借给别人呢?
为能在3日内设法借到4000块钱,临近夜阑人静的子夜时分,邓拓夫妇俩把所能想到的办法全都捋了个遍,把平时走得近点、相处得来的朋友,几乎挨个地排了个遍,因种种原因,一一作罢,至此一筹莫展,没有一点儿着落。
就在邓拓责备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刚才漏排的另一个人来,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好友吴晗(其时吴晗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任上,与在北京市委任职的邓拓,是好同事、好朋友),他的眼前恍若闪烁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可借理由是:前不久吴晗出版了《朱元璋传》《历史不曾远去》《海瑞罢官》等著作,听说稿酬颇丰,跟他暂时借用4000元,大不了把自家人日子过的节省点,自己幸苦点也像吴晗那样出版2本书,挣点稿酬,尽快还给吴晗家,不就成了。邓拓很自信,只要开口,相信吴晗不会不给面子的吧?
可是夫人丁一岚持不同意见,她说她跟吴晗夫人袁震也是多年的好友,但她家实际情况也不尽如人意的。吴晗出书是会得到一定的稿酬,可袁震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多少年卧床不起,吃的贵重药多为自费,消费很大,吴晗的稿酬都花销在这上面了,找吴晗借钱真是难为他了。
夫人方才一席话说的有道理,邓拓点头称是:吴晗确实很辛苦,整个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人都知道的,里里外外一把手,儿子和女儿又都在上学年龄,卧床不起的夫人常年需要他照顾,他是全家的顶梁柱,一切的家用支出全靠他挣得,无人可以取代他,借不得,借不得的。
夫人的提醒,打消了邓拓预备开口向吴晗借钱的念头,这就好比让他本来认为最有希望的一线之光,宛若被一盆冰水当头浇灭似的。
好在邓拓认为自己心中的希望之光还在,3日后一手交钱,一手取画的信念还在,除非白老先生食言,他的怀瑾握瑜的人格魅力,绝不会因借款困难重重,而损毁和丢失。
不光是这次借款购买古人真迹画作,即便是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烦心之事,邓拓基本都能化解而不留遗憾。他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此时对苏轼孤品画作的志在必得,邓拓丝毫没有妥协和动摇。
邓拓见到夫人有了困意,不断地打盹,就叫她先回卧室休息去,毕竟明天还要按时上班。他要一个人再静静地思考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以变通的办法,他不信活人会被尿憋死。
3日后5000元取画款,一定要落实到位,这是必须要完成的硬任务,决不能让到快要到手的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错失良机,落下此生遗憾。
办法就在自家储藏室的藏品里
翌日早晨起来,邓拓在他家储藏室门前经过,突然想起妙招来了,他叫来比他起床更早的夫人丁一岚,他似乎又恢复了昨日晚餐时的兴奋状态:一岚啊,储藏室里不都是我们这多年来积累的藏品吗,何止是5000元的价值啊?办法有了,就在储藏室的藏品里。
邓拓家的藏品跟谁作价套现呢?
此时,北京荣宝斋的词条,进入了邓拓脑海的“百度网”:他赶在上班前,把电话打到了荣宝斋总经理许麟庐家中,他们在文物方面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放下电话的邓拓,脸上先前密布的愁云散去,和那天北京的天象一般,晴空万里,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丽日宜人,心情愉悦。
荣宝斋掌柜许麒庐,在电话那头,一口答应邓拓用家藏古董作抵押,暂借5000元款子的请求。
因为,邓拓在电话里把他意外发现苏轼传世孤品画作的事由,告诉了许麟庐。他不隐瞒他,他俩在工作之余,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探讨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文房四宝,很少涉及儿女情长一类的话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
来自邓拓的重大消息,一下子促动了许麟庐对文物尤其敏感的神经。以他对邓拓这汪“文塘”深浅的了解,他完全相信邓拓的慧眼和鉴赏古董的能力。在他们多年的交往中,邓拓曾帮助荣宝斋成功鉴定过几件吃不太准的重要文物,例如明代沈周设色山水轴;元代吴镇的水墨山水轴等,荣宝斋当时在综合参考邓拓鉴赏意见基础上,排除异议,确认真迹,实践证明邓拓的鉴赏能力非同一般,被许麟庐赞誉在为长了一双“鹰锥般的厉眼”。
既然能够相处到好友及挚友的层级,邓拓对许麟庐的了解,也是谙熟于心的:
许麟庐1916年出生于山东蓬莱,父亲是清末举人,自幼秉承家学,习书作画,赋诗撰联,精赏擅鉴,是我国集书画评鉴藏五项全能于一体的著名艺术大家。新中国成立后,邓任人民日报社长,许当坐落于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总经理,书画会友,渐成挚友,胜过管鲍之交。
这里需要补充交代一点的是,虽然许麟庐非常时期也受到不小的冲击,但他没有像邓拓那样走极端,而是咬紧牙关、宠辱不计,赢来了人生新的春天。许麟庐无疾而终,于2011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今日邓拓只推迟了半小时下班时间。说来也巧,夫人丁一岚前脚刚跨进家门,邓拓后脚紧紧跟上,他俩相视而笑,都说这是他们住在这儿以来从未有过的巧合,一阵喜悦感像北京果脯甜蜜着他们的心田。
人有喜事,心心相映,有时候就是这般的灵验。
邓拓把荣宝斋掌柜许麟庐暂借他5000元,先把苏轼孤品画作拿到手的事,告诉夫人丁一岚,就等于说购买画款有了着落,不需要再东借西欠了,更何况想借也无处可借。与此同时,家里那点不足1000元的生活费,也不需要动用了,丁一岚觉得这事多好哇,高兴的她要跳起来。
其实,丁一岚昨晚心里正烦着呢,即便是借到4000块钱,把家里的备用金贴进去都不够,又才发过工资,弄的捉襟见肘不说,怕是一日三餐也不能保证呢。邓拓家如真的三餐不保,可能还没人相信的吧?毕竟他是高级干部家庭。
丁一岚问邓拓:你后天下午跟人家白老先生拿画,荣宝斋什么时候把钱借给你呢?
夫人所问与邓拓接下来所讲,又是一个巧合,原来邓拓和许麟庐借钱,不是夫人理解的借款,而是拿家藏古董作抵押。明天正好是星期天,许麟庐带上5000现金和三个鉴定专家,约好上午九点来到邓拓家,任选可抵押5000元藏品的家藏古董,待日后有偿还能力时赎回。
邓拓搞文物收藏,丁一岚平时跟在后面增知长识许多,自然也懂得了不少,说她是行家里手,亦不为过的。
她问邓拓:像你收藏的古代名家一些珍贵字画,包括“珠山八友” 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等这些明清名家的瓷器,你也让许麟庐他们任选?我建议你在他们来到我家之前,收点起来吧,其他藏品任他们挑选。
邓拓莞尔一笑:一岚啊,你跟我生活那么年了,我是那种鬼鬼祟祟的人吗,他们如选了“珠山八友”的东西,我可以请求不选,或尽可能少选,至于古人字画,他们即使选了,我也不会给的,我这藏室里能够抵押5000元的古董多着呢。
邓拓认为,许麟庐若不同意他用藏品抵押方式,帮他解燃眉之急,苏东坡的宝物,千年邂逅,对他来说不啻是一场空欢喜吗?那种一生的遗憾像个大窟窿,何时才能再有机会得以弥补和填平呢?
丁一岚,完全赞成邓拓的意见,尤其是邓拓始终不曾改变过的瑰意琦行的优秀品格,一次又一次地感动过她,今日她的这种感动,格外尤甚。
于是她动情地抱紧邓拓,把头依偎在他的胸前,聆听他豁达开朗的胸襟,传递给她的铿锵有力的律动与音旋!
第二天上午9点,许麟庐带着耿宝昌、徐邦达、刘九庵等3位鉴定专家准时来到邓拓家中。
邓拓家的住房是根据省部级标准稍偏高安排的,北京典型的砖木结构四合院,建于雍正6年(1728年),按邓拓的掐指算,该建筑已伫立于此233个年头,他家从原先的铜罗巷迁居到此也近6个年头。由于配有司机与规定的公务人员,房子相对很宽敞的。
许麟庐一行4人跟邓拓夫妇寒暄之后,草草地吃点主人事先安排的水果、点心和茶水,就跟邓拓夫妇进入古董储藏室,预备选些相当于时价5000元抵押藏品,选什么价值的藏品,许麟庐的意见为主,耿宝昌等3人可作些参考性的建议。
邓拓的家藏古董,坊间早有丰藏的传闻,但谁也没机会亲眼见过。今日一见,让许麟庐等为之一振,大饱眼福,多得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从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到秦汉时瓦当、坛罐:从历代书画作品及明清时的陶瓷器等藏品,应有尽有。其中南朝的羊真孔草、萧行范篆这样的书法古董,他都有所收藏,这是非常不易的事情。
足可见邓拓的文物收藏,完全地融进了他生活之中,可以说文物收藏成了他的第二生命,这些随处可见的藏品,就是最好的佐证。
其实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便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真正懂得文物收藏的人也不多见。那时捡漏子,是如今上了年岁仍健在收藏家们,谈得最为眉飞色舞的往事。现在的收藏家们几乎捡不到一个漏子,若说能捡到的话,大多为皆为高科技的仿品、作假赝品。真品有的,都在各级各类博物馆藏着,那是属于华夏民族共同所有的国之瑰宝,是供人们前往观赏的古董,也是今人跟古人对话的方式之一,见证了中华文明与文物,一路走来的博大精深,可以激发人们自豪感与爱国的热情,根系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这就是文物古董的意义之所在。
不一会功夫,许麟庐他们从邓拓家林林总总的藏品中,选到了22件,多数是陶瓷器和瓶盘之类,“珠山八友”的瓷器仅选一件,书画古董免押,以此数量的藏品抵押5000元的借款。
可是笔者要插话的是,现如今这22件珍品,绝不是5000
元的市场价值吧?若现在变现成交,每件都有可能是个天文数字,亦为毋庸置疑的!
抵押藏品的清单列好了,22件古董的名称、年代,抵押单价,清晰无比,末了合计数阿拉伯数字加汉字大写,只要双方签字画押,5000元现金即付邓拓夫妇。
这时邓拓夫人丁一岚,呜呜地哭泣起来,流着眼泪对许麟庐等说道:你们拿的这些抵押品,其实我一件都啥不得离开我的视线,件件堪比比我和邓拓的孩子,虽然它们不会说话,但跟我俩的感情深着呢。哪一件不都是我和邓拓两人省吃俭用得来的啊,有时候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我们家是名好听、穷收藏,日子过的紧巴巴的。
许麟庐见邓拓邓夫人那么疼爱家藏古董,旋即安慰道:夫人啊,你的心情我懂的,但这是抵押,不是变卖,明天下午邓书记拿钱购买苏轼画作,那位白老先生家因生活所迫卖古董,那才叫变卖。等你们日后有了偿还能力,22件藏品完璧归赵,我向你保证,荣宝斋不会少你一件,少一罚十!
22件藏品正式做了抵押,拓夫妇拿到了荣宝斋现金5000元,那时还没有百元面值的纸币,最大面值10元,堆叠在一起厚厚的一摞子,在当时就是名副其实的巨款,接近邓拓夫妇年工资收入的总和
邓拓夫妇一起前往迎接“苏东坡”
夫人丁一岚知道邓拓没经手过这么钱,平时家里收入与支出,也都是她理财,邓拓从不过问。有鉴与此,丁一岚明天下午要跟邓拓一起去取画,迎接“苏东坡”到自家,邓拓同意了,他俩又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对视着会心一笑。
第二天下午邓拓要把大前天布置的工作做个检查,有布置有检查是邓拓同志多年来不变的好习惯,亦因此常常受到老北京市委的人好评。
不过邓拓同志这一次的因公例行检查,多了个一手付款一手取画的美差。虽说钱是他用家中藏品做抵押借来的,但他却始终为此生能够有幸收藏到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而兴奋不已,沉浸在无比慰籍和幸福的氛围中,他仿佛觉得自己是跟苏东坡最亲近、最有缘分的人。
还是那天的司机,不过车里多了个人,那就是他的夫人丁一岚。说来也是个难得的巧合,夫人她们播音组三班制,这天下午摊她正常休息,不需要请私假,多一个人从旁照应,谨慎起见,没啥不好。
白老先生和邓拓都是守信的人,规定的时间,不变的东交民巷不远处的胡同口。再次相逢的他们,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热情催生热量在他们两人身体间相互传递着,全然驱除了北京冬日凛冽的寒风对人的侵蚀感,好一阵子乐呵呵地客套寒暄,俨然成了结情很深的老朋友似的。
站在一旁的丁一岚,看到他俩仅有过一次的谋面,就变得如此热情和熟悉,全无陌生感,心里也多了几分踏实,使她感觉到邓白两人之间买卖是靠谱的,并且片刻就会有成交结果的出现。
邓拓毕竟是个大知识分子,知书达礼之人,遂将伫立一旁的夫人向白老先生做了介绍,他俩亦礼节性地握了手。白老先生赞美了丁一岚,说邓干部的夫人有风度、有气质,一表人才。若白老先知道丁一岚是台花,可能赞美之词会更浓丽一些的。毕竟藏有苏轼《潇湘竹石图卷》的白老先生,猜想家学非比一般普通人家的吧?变卖祖传古董完全是出于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况且在上世纪60年代初3年自然灾害期间,变卖家当古董,比比皆是,能有值点钱的当家变卖保性命,在那时算的是比较幸运的人家了。
今天的白先生不再是大前天伫立胡同口的兜售者,而是有了已知客户的“供货商”。角色变了他人也变了,不再是穿着破衣烂衫、面目清癯的可怜兮兮的瘦高个子的老者,变成了衣着整洁,精干利落、全没了穷酸潦倒般模样的人,与大前天相比较迥若两人,这让邓拓刮目相看,心头平添了些许对白老先生的敬意之感。
由于事先讲好今日一手付钱一手取画,白老先生不用再像先前那样徒手抱画、走街穿巷漫无边际地卖画,而是把画装在一个精美的木盒式手拎箱里,上有竹石雕刻的图案,与古画相匹配的收藏佩饰,据说是用百年榆树木制做的,木质坚韧耐腐,表面颜色呈深栗色,古色古香,使人一看便知其有了比较久远的年代。一般人家绝不会有这类箱子的,只有收藏之家才会用到的,因此箱子的考究说明家藏古董的珍贵,物以稀为贵的珍品,自古藏家的钟爱。
由于是私下买卖,三人因地制宜地另选了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付款取画。白老先生快速地把画从精美的箱子里取出,旋即展开画卷,邓拓夫妇目不转睛地观赏着:古色古香的画作,对于丁一岚来说是初见,但她的直觉告诉她,苏轼原作墨汁色韵及画面的沧桑感,就该是这个样子的;而邓拓是重见,并在之前对照有关史料做了深入研究,只要白先生守信不调包骗人,那幅《潇湘竹石图卷》就是邓拓大前天下午见到的那幅画。
一贯行事深思熟虑、细针密缕的邓拓,对这个5000元的大买卖是用了防备之心的。那天在白老先生全然不知情况下,邓拓悄悄地在画作背面留下一道指甲印迹,只要这道指甲印迹留在画背上,证明就是他第一次看到那幅《潇湘竹石图卷》。邓拓看到他留在画作某处识别记号,清晰可见,兴奋得翘起大拇指夸赞白老先生是好样的。白老先生虽然不知是何意,但还是礼貌地对邓拓的美赞表示了感谢。
对初次相识的人防一手,完全出于5000元大买卖的需要,更何况买画的钱来之不易,要不是荣宝斋给足了邓拓的面子,这笔巨款到哪也无法借到,更何况那时又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极度困难时期,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谁家还有多余的钱借给别人买古董呢?
这时邓拓正式发话了:白老先生,不好意思,我夺人所爱了,请您老把这5000元卖画款收下,今后这幅画就归我收藏,谢谢您信任我能够收藏好你家祖传的老古董,我相信今生有缘之人,一定能后会有期的。我还有公务要处理,我们夫妇跟您再握个手,对我们双方买卖愉快成交表示庆贺。
邓拓夫妇提着白老先生那只内装《潇湘竹石头图卷》精美的藏画箱准备离开时,但见白老先生老泪纵横,凄楚言之:我卖给你们的这幅家藏古董名画,要不是家中断炊,我哪舍得出手啊?这幅古画是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画的,在我家不知传了多少代人了,许多不识货的人说是假画,我有幸遇到您这位懂得苏东坡的邓干部,不还我一分钱的价格,一口答应愿意用5000元买下这幅画,还给我加了60元钱,您救了我们全家八口人的性命,我代表我全家人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您和您夫人是天底下心肠最好的人。白先生说罢向邓拓夫妇敬了个深鞠躬礼,然后挥挥手说:你们都是大忙人,快走吧,让我在这里再站会儿目送目送你们这样的好人!
载着苏轼《潇湘竹石图卷》的小车行驶了好远,邓拓夫妇透过车窗看见白先生仍一动不动地站在胡同口,经受着室外的寒风袭面,手还在不停地向车子远去的背影挥动着。见此情景,邓拓夫妇相视无言,一阵为民而忧的酸楚感在他们善良的心头掠过:
国家困难时期老百姓日子过得多艰难啊,穷得纷纷变卖家当保命,就像当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从陈国到蔡国途中遇到断绝粮食的事情一样,陈蔡之厄的生活困境真的要尽快结束才好,还百姓衣食无忧的生存环境。
潇湘竹石图中华民族共同所有
邓拓不惜一切代价从民间收藏到的苏轼《潇湘竹石图卷》,为了进一步确定是真迹,他在夫人协助下,展开画轴后测量画卷长度为106厘米,幅宽28厘米,其尺寸与史料记载是一致的。邓拓好比吃了第一片定心丸,心里踏实无比。
纵观展现在眼前的苏轼《潇湘竹石图卷》,邓拓夫妇感觉苏轼不仅是清雄豪放的一代诗人,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丹青妙手,他写竹若风尽摇,石如白云出岫;书则豪放跌宕,丰腴遒健,浑厚古朴,整幅《潇湘竹石图卷》信手拈来,自成一格,表现出苏轼绘画方法上的革新精神与创造性,在北宋那个时代他就是新型文人画风的开拓者和导师。
邓拓一边欣赏画作,一边给他的夫人丁一岚描述苏轼的绘画技法。邓拓告诉夫人:苏轼画石用的是飞白笔法,画竹用书法艺术中的横竖撇捺而加变化,烟水云山、远树则用淡墨点染,气韵极为生动,尤其是末端的“轼为莘老作”、“翰林处士苏氏子瞻”题款,简炼亲和,与苏轼的诗文风格颇为一致,至于那画面上长达212字的诗文,是明代大才子杨慎为苏轼《潇湘竹石图卷》题跋所书,为其增色无限,令人遥想千年东坡先生的亮节遗风,实为世代不朽画作。
后经荣宝斋掌柜许麟庐、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鉴赏家刘九庵、耿宝昌等名家把脉“会诊”,证实的确是苏轼绘画作品真迹,作品产生年代大约在1081年至1084年之间,也就是苏轼被宋神宗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所作。至此,邓拓心中尘埃落定,大功告成!
吴仲超院长很是羡慕邓拓的这件稀世藏品,给予很高的评价:邓书记,您的这件藏品说不准就是苏轼存世画作孤品,故宫博物院藏有唐代田园诗人王维的山水卷,但到目前为止故宫还未收藏到苏轼存世画作真迹藏品,这个遗憾现在被邓书记私人收藏所弥补。
能够收藏到苏轼的《潇湘竹子石图卷》,对邓拓来说就等于收藏到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珍贵古董,幸运之神用会逢其适的方式,将邓拓和苏轼这两个不同时代抱诚守真的文化人,以画为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到底结的是哪辈子缘呢?邓拓直到临终前都没有弄得清楚。但邓拓绝无杯弓蛇影自扰,只有“天意”二字的无解注脚,伴随着他今生喜不自禁的一份自豪的收藏。
或许历史和现实是对邓拓的一个不忮不求的信任,上苍仿佛完全地相信邓拓有种无私无畏的崇高境界——他会居仁由义,跳出宝贝仅仅自身拥有的俗圈,偏信他会迟早有一天让这一绝世真品成为国之瑰宝。这可能就是苏轼《潇湘竹石图卷》经千年民间流转,最终以花落邓家的结局,不易之论地完成它富有传奇色彩的收官流转程序吧?
随着收藏苏轼《潇湘竹石图卷》的兴奋感慢慢平复之后,一天邓拓突然想起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春日书怀》里“眼前名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的千古名句,他的境界随之变得从未有过的宽旷畅达,他要把这一珍宝捐献国家,并经过和夫人丁一岚多次沟通求得一致共识:苏轼是北宋文化旗手,他的绝世真品《潇湘竹石图卷》,不但具有历史纵深感,而且文物文献价值非常之高,应该属于中华民族共同所有,不属于我邓拓个人家藏所有。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公元1965年9月28日,即新中国成立16周年的前夕,邓拓夫妇把北宋伟大的文学家、诗人、书画家苏轼生前创作的设色山水卷《潇湘竹石图卷》,无偿奉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填补了故宫无苏轼绘画藏品的空白,吴仲超院长紧握邓拓的手深有感慨地说:千年苏东坡的绘画真迹图成国家所有,故宫博物院不会忘记邓拓同志和夫人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
从此,这一国之瑰宝在邓拓私人收藏了4个春夏后,以轰动般的效应走进了故宫藏室和公众视野,成为当年的一则颇有影响的新闻。如今中外游人到故宫参观,每逢展期就能目睹到苏轼《潇湘竹石图卷》的真迹图古韵风采。
一代文化名人邓拓同志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当年和夫人丁一岚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苏轼《潇湘竹石图卷》,依然呈现在络绎不绝的前来故宫参观的中外游人视线里,仿佛画中的苏轼和画外的邓拓,两个不同时代人的身影互动着、重叠着、亲切交流着,相敬相亲,永不分离!




